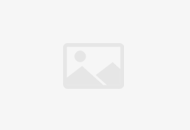自1888年10月24日开始,
梵高与高更在法国一个叫阿尔的小镇一起度过了62天。
作为纯粹的艺术家,两人希望抛弃一切,
给世界留下“一份新艺术的遗嘱”。
梵高和高更,生于同一个年代,相差五岁,历史有时是以极端冲撞的方式激射出创造与美的灿烂火花。
他们的生命中一瞬间曾经有过交集,不过很快就分开了。
在那之后,梵高割掉了自己的耳朵。
同样的“自画像”主题,一位化身为日本僧侣,一位自喻为悲惨者;
同样的“夜色咖啡厅”,他画下了令人窒息的寂寞,他涂抹了深沉的冷静;
一束向日葵,绽放于热烈的等待,凋零于无尽的思念……
他们之间,是触目的色彩,是个性的笔端,是一段又一段满溢着,期待与失落、对立与心痛的故事……
他们在一个时代相遇,也在一个城市相遇,他们相遇在文明的高峰。梵高一八八七年在巴黎与高更相遇,很短的相遇,然后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梵高去了阿尔,高更去了布列塔尼。他们对那一次短短的相遇似乎都有一点错愕──怎么感觉忽然遇到了前世的自己。
高更认识梵高的那年,正是两个人都陷于生活最低潮的时刻。高更无法照顾远方的妻儿,常常自责绝望到要结束生命;梵高与妓女西恩刚刚分开,所有宗教的狂热与爱的梦想全盘幻灭,孤独到巴黎投靠弟弟。
两个完全相似的绝望生命,却共同燃烧着艺术创作不可遏止的热情,他们似乎在对方的绝望中看到了自己的绝望,他们也似乎在对方燃烧着热情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的热情。高更与梵高的相遇像不可思议宿命中的时刻,相互激荡出惊人的火花。一八八八年十月,他们重聚在阿尔,要一起共同生活两个月,更巨大的撞击将在一年后发生,他们历史的宿命纠缠在一起。
意气风发、自由奔放且充满自信的高更是梵高向往的对象,而和高更共同生活的梦想则与日俱增。此时梵高三十五岁,高更四十岁。梵高对高更的感情是对前辈的尊敬与敬畏、对伟大艺术家的向往与嫉妒以及对朋友的热爱与不安等,复杂交错。在高更决定前往南方画室时,梵高兴高采烈,欣喜若狂。长久煎熬的孤独感得到缓和,因为只要有了高更,今后再不用别人指明方向了。准备迎接高更的那个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梵高最幸福的时刻。
为了高更要来阿尔,梵高刻意布置了他的房间。
这张《房间》像是梵高布置的新房,用来庆祝一种新生活的开始,用来准备迎接一个全新的温暖的生活,明亮的暖色调占据了画面大部分空间。
这是一个梵高梦想的“家”。他是为高更的到来而布置这个“家”的,那么,他是以多么强烈的欢欣与兴奋在经营这个家。
为了迎接高更到阿尔,梵高处在一种高亢的情绪中。他读了一些有关日本的文学描述,他一知半解地向往着遥远的东方,东方的僧侣,用一生的苦修,把自己献给信仰;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修行成永恒不灭之佛。梵高的《自画像》中这一件最强烈,又最平静,极其素朴,又极其庄严。梵高自己很看重这件《自画像》,他把自己送给高更,并且比喻为日本僧侣,献给永生之佛。
遥远的距离或许产生了最美的友谊的幻想,梵高创作了一张杰出的自画像,送给高更;高更也画了自画像,送给梵高。他们相互激荡出了创作上的火花,两人的风格都逐渐达于巅峰。梵高狂热渴望高更到阿尔,两人共同生活,一起画画。他为高更准备房间、家具,甚至特别为高更的房间手绘了墙壁上的装饰。梵高为高更画了《向日葵》,他要把这南方阳光下的盛艳之花送给高更作为迎接他到来的礼物。
向日葵像在阳光中燃烧自己的花朵,冶艳、顽强、热烈、剽悍,使人感觉到旺盛而炽烈的生命力。梵高寻找着阳光,从郁暗的荷兰到巴黎,又从巴黎一路南下到阳光亮烈的阿尔,梵高自己就像是追逐阳光的人。当时高更在布列塔尼贫病交迫,梵高呼唤高更前来,他觉得可以照顾这个落魄潦倒的朋友。
葵花插在陶罐里久了,花瓣很干,像乱草飞张,葵花的中央是一粒一粒的葵花籽,赭褐色密密的小点,使花蒂显得更顽强。这是炽烈强悍的生命,但被截断了,插在陶罐中,好像有一种顽强的对抗,好像生命在最后死亡的时刻依然如此热烈地燃烧。这样灿烂的花,这样的明亮、热情,用全部生命来燃烧的花,梵高指名是要送给高更的。
他希望把这些向日葵挂在高更的房中,他为高更准备了最好的房间,他一再跟朋友描写他如何为高更布置一个优雅的住处,他把自己画的向日葵挂在墙上,等待高更到来。“向日葵”是梵高最纯粹的热情与爱,那些明度非常高的黄色,事实上是大量的白色里调进一点点黄,像日光太亮,亮到泛白,亮到使人睁不开眼睛。梵高也许不知道他画的正是他自己的生命,这么热烈,无论是友谊或爱情,都使人害怕。
梵高在长久巨大的寂寞中渴望着一种温暖,他也许分不清楚那是友谊的温暖,或是爱情的温暖。但他确实在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很具体的对温暖——家的温暖、人的温暖的渴求。床与椅子,都像是一种等待,等待某一个生命里特定的对象。梵高显然在渴望一种平凡的幸福,一种爱与被爱的幸福。画完《房间》,十月二十八日,高更来了。
高更在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了阿尔,一下火车,连车站咖啡馆的老板吉尔努斯先生都认出了他,因为梵高早已拿着高更的画像四处宣传了。高更走进梵高为他精心准备的房间,看到墙上为他画的《向日葵》,高更是什么感觉?一八八八年十一月,高更曾经为梵高画一张像,画像中梵高正在画《向日葵》。
在一八八八年十二月,梵高画了《高更的椅子》。“椅子”不再是空的等待,“椅子”有了专属的主人,椅子上有着主人不同的物件。墙壁上有一盏亮着的灯,一圈晕黄的光,这是深夜,高更似乎正在椅子上看书,但是离开了,椅子空着,灯光、烛光兀自燃烧。
《梵高的椅子》,非常单纯,地面上是褐色方砖,一把木椅,在《房间》中出现过。这把椅子是欧洲民间最粗朴的家具,但是简单、顽强、有力,像是在对抗什么,牢固不肯妥协,四个脚的木腿像柱桩一样顽强,没有一点退缩与让步。这两张“椅子”只是他们偶然误解的位置,他们偶尔一坐,又各奔前途,“椅子”像是短暂梦想的记忆。
梵高精神亢奋的狂热并没有感染高更,他们日日夜夜在一起作画,常常画同一个主题,同一片风景,但是观看的方式却完全不同。梵高画过阿尔的《夜间咖啡屋》,是彩度极端对比的红色的墙、绿色的弹子台、黄色的灯光,有一种陷入精神高度亢奋的错乱。这是梵高走向梦想的巅峰,也是梵高走向毁灭的开始。他已经开始用燃烧自己来取暖,用燃烧自己来发亮。
高更同样画了《夜间咖啡屋》,他以咖啡屋老板娘“吉诺夫人”为主题前景,也用到墙壁的红、弹子台的绿,但是色彩被一种黑色压暗,和梵高画中强烈的对比不同,高更的画面有一种深沉的冷静,他好像要刻意过滤掉梵高画中过度高昂的情绪。
但他们的相处并不和谐,生活如此紧密的关系,太多冲突,太多摩擦,太多琐细的现实细节会使两个敏感纤细的心灵发疯,会使两个自我个性强烈的心灵发疯。高更事后描述梵高要发疯了,他常常半夜忽然惊醒,看到梵高向他走来,凝视着他,又无言地走回自己的床上睡倒,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梦想在现实中变得荒谬、扭曲、琐碎而难堪。
就是在阿尔这段时期,高更在十二月写了一封信给画家贝纳,谈到自己与梵高的巨大冲突:我在阿尔完全失去了秩序。我发现一切事物都这么渺小,没有意义,风景和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