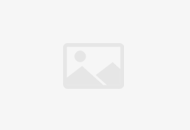大约在“六世余烈”的雄主出现前的两百多年里,大秦帝国并无鲸吞天下的蛛丝马迹,甚至灭国之祸都只在旦夕,先是被晋国死死压制,后又被魏国全取河西之地,文化上更是处于鄙视链的底端,其实他们好歹是周天子亲封的西方霸主,也是“祖上曾经阔过”的。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谏逐客令》
李斯为劝谏秦王收回“逐客令”,第一个就搬出了今天的主角--春秋五霸之一(史记版本)的秦穆公,上文提及他礼贤下士于东方,找来了振兴秦国的五位大才,并拓地千里,称霸西戎,仅此二条一代雄主之姿便跃然纸上,但其优秀还不止于此。
冬,晋荐饑,使乞籴于秦... ...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汎舟之役”。--《左传.僖公十三年》
所谓“汎舟之役”并非战争,而是后来为解救晋国饥荒而慷慨解囊,河面上运送粮食的船只从秦国首都雍城一直连到了秦国的绛地。被援助的对象则是他一手扶上君位的晋惠公夷吾,这位大舅哥先前刚刚赖掉了将“河西五城”作为报酬的承诺,可谓毫无信义的典范,嬴任好却不计前嫌,一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堪称后世君王求仁的典范。
两年后秦国绝收,遂求救于晋,夷吾还真是头白眼狼,他派了一支军队投桃报李,本人则亲任主帅,可惜带来的却不是粮食,而是明晃晃的兵器。
被欺负到这份上,嬴任好终于出离愤怒,双方在韩原大打出手。从结果来看,晋惠公的趁人之危之举最终成了“千里送人头”,本人被当场生擒,虽然后来被放了回去,但太子圉当了人质,河西五城也归入了秦国版图,总算是摸到了殽函的门边。
但从过程来看却并不轻松,当时秦穆公为晋兵所围,左支右绌,铠甲破碎亦不能突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支三百多人的“野人”队伍从天而降,他们死死护住穆公车驾,直至援军赶到完成反杀。
所谓野人并非来自神农架,而是先秦特有的称呼:住城里的叫国人,多为宗室和各家族成员,城外自生自灭的则叫野人,他们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相应的也无需承担兵役方面的义务,那这回为何如此卖力呢?
昔者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缪公自往求之,见野人方将食之於岐山之阳。缪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女也!”於是遍饮而去。--《吕览.仲秋纪第八.爱士》
事情起源于某次出游时车驾右边的马逃跑了,待找到之时却发现一群农夫正啃得津津有味,他们虽然桀骜不驯,但毕竟不是自己的马,还是知道对错的,此刻看着漫山遍野的军队一时间有点回不过神。这时候秦穆公发话了:“听说吃马肉不喝酒是要伤身体的,我很担心你们”,随后他下令将车上的美酒搬下来,后者亦不推辞,吃饱喝足后扬长而去。
做人做到这个份上,应该说怎么夸穆公都不为过了,所以出现在韩原的秦军不只是复仇的哀军,更是无可辩驳的正义之师,其胜可谓当矣。
而除了为人称道的品德之外,后来被东方六国当成蛮夷和虎狼的秦人似乎很有深得礼乐精髓的味道。
话说时过境迁,秦穆公决定为晋国拨乱反正,奔波了十九年的姬重耳终于第一次与妹夫见面了。虽说大方向早已各自心知肚明,但条件还是要谈的,而跟夷吾直接许诺割地不同的是,双方的会面犹如一场唱诗班表演,各自朗诵了几首《诗经》的经典后就宾主尽欢。
▲当年看电视剧时完全是云里雾里。
明日宴,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
菽便是豆子,秦穆公并非邀请重耳一起干农活,而是通过“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之句暗示对方我不光能够赠送你车马,还能让你成为晋侯(玄衮即黑色的诸侯正式礼服)。重耳则马上下堂拜谢(降拜)并回复了一首《黍苗》,借“芃芃黍苗,阴雨膏之”之语表示感谢。
▲国宴赋诗往事来自《国语.秦伯享重耳以国君之礼》所载,各位可自行搜读,先人之风采实令后人汗颜。
几个回合之后重耳最后以《沔水》中“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之句表达了他就像河流一样,奔向宽厚如海的秦伯的想法,言外之意当以秦伯为尊,行将报答,后者则哈哈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谈生意也这么有艺术,将当年的秦人定义为蛮夷显然是过分了。再后来秦穆公后来赦免殽山败北的孟明视三将并成功复仇,随后向西发展,终拓地千里成为西方霸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为君和道德上都堪称完美人,其葬礼上却出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左传.文公六年》
穆公卒,葬于雍,从死者百七十人。--《史记.秦本纪》
近两百高级贵族贤臣伴随死去的雄主缓缓走进了殉葬坑,朝堂为之一空,其中就包括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子车三雄”。按照殉葬的出发点,嬴任好是想让臣子们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替他出谋划策,征战沙场,然而他似乎忘记了秦国的社稷更需要这些人才。
秦风《黄鸟》缅怀了子车氏三子以一敌百的战场雄风,在辛辣讽刺国君之余更悲痛地唱到:“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如此“苍天”,留他何用?
左丘明更是不依不饶地追讨:“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活该他当不了齐桓晋文级别的霸主!
原来在这一刻,嬴任好同志生前所有的优质“人设”就此归零。
话说秦人之祖恶来本为商臣,沿用人殉之旧俗仿佛有所渊源,然其先替周天子西陲养马而为附庸,护送平王东迁之功而立国,礼乐文化的四百余年熏陶仍未令他们放弃蒙昧,而更可怕的是,秦穆公及后继者还远远低估了这一“理所当然”之举带来的危害。
▲稷下学宫的风采,终秦国五百年都未能望其项背
首先,平王东迁之后关中地区文化缺位本是事实,秦人重用外客实属不得已之举,《逐客令》中提及的几位亦只是一流而非顶尖人才,只不过秦人的舞台向来要大一些(人才稀缺嘛),但如果百里奚和蹇叔这些老头子不是提前寿终正寝,此番怕也不能幸免。
反观东方诸国,周公旦“敬天保民”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对人文的尊重早已超越鬼神,而人才和生产力的短缺亦是内因,除了少数奴隶之外,陪葬的多是器物和车马,鄙视链很快形成,后来秦孝公曾痛心疾首地说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碌碌无为的秦景公僭越了“黄肠题凑”的天子墓葬规格,还COSPLAY了秦穆公人殉的力度。
其二,秦人此后到景公时代,人殉都没有断绝过,贵族也争相仿效,其陪葬人数次数在两周时代都堪称一枝独秀。殉葬的心理阴影导致了“士子百年不入秦”的恶果,大量的秦人也因此远离故土并朝着文明的方向迁徙,秦国也因此而人口凋零,人才稀缺。
秦穆公之后,秦国的国力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终春秋之世再无上佳的表现,反倒被晋国彻底阻隔了与中原的交流,文化程度一降再降,终于在战国初年成了人人鄙视的蛮夷。农业和经济也随之受挫,如鲁国推行“初税亩”与秦人的“初租禾”相隔了近两百年,当东方六国大步走向文明之际,秦人却几乎无可避免地滑向了深渊。
韩非子曾言“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为历代秦君的荒唐之举做了精辟的总结。
总之,在位三十八年的秦穆公或许是老糊涂了,又或许是纯粹的自私和虚伪,曾经对人才的不拘一格变成了打包带走,礼贤下士变成穷凶恶极,宽容变得冰冷,当厚重的灵柩和陪葬的棺材缓缓告别人间时,一起下沉的还有秦国的命运。
或许,唯二值得说起的是还是秦孝公和商鞅,前者眼巴巴地看着宗庙里那个显赫的名字,终于想起了曾经的不二法门,一纸《求贤令》下终找来了走投无路的商鞅,开启了外客赴秦的先河;至于后者,其深刻变法的前提不止是国君的鼎力支持,唯有光脚两百年的秦国才有接纳一切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