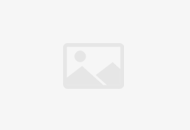连坐法相较于缘坐法,产生的时间更早。在商鞅变法中,商鞅为了巩固君主统治实施了什伍连坐法,这是古代连坐法的开端。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在连坐产生之初,株连的范围较广。缘坐至北魏时,始见于典籍的记载。缘坐出现后,连坐成为与之相对应的概念。连坐专指株连与案犯无亲属关系之人;缘坐专指处罚与主犯有亲属关系的人员。连坐与缘坐明确区分的情形在唐代被正式确立下来。然而“缘坐”产生后,即存在与“连坐”混淆的情况,实为历代法律施行中共有的现象,金代这一现象更是较为常见。因此研究金代连坐法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厘清“连坐”与“缘坐”这一组相似法律专业术语的含义及其在金代的具体情况。
一、金代的“连坐”与“缘坐”
1.连坐的出现及其定义
在中国古代,“连坐”一词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这是“连坐”作为具体法律规定出现的最早记载。唐代是连坐法比较完善的的时期,《唐律疏议》中“连坐”条文一般是指职官连坐,如:“其官文书稽程,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并原之,主典不免;若主典自举,并减二等。”现代对连坐的定义主要关注其株连性,对连坐范围的划定比较广,形成了广义的连坐。《中国古代法学辞典》中对“连坐”的定义为:“也作‘相坐’、‘缘坐’。
因一人犯罪而牵连亲属、邻里、同伍以及其他与之有联系的人都承担罪责的刑法制度。”《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对“连坐”的定义为:“因他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又称相坐、随坐、从坐、缘坐。”孙英民认为“所谓‘连坐’,就是触犯法律的行为人及与该行为人有某种程度联系的人员并行坐罪的刑罚。”综上,战国时期与唐代的“连坐”并非以血缘作为纽带,常见的连坐主要是邻人连坐及职官连坐。现代对“连坐”的定义则较为宽泛,讲求的是与触犯法律者有联系的人员就将受到处罚,与案犯有关的人员连带受刑都被称为“连坐”,而亲属之间的株连也属其中。
2.缘坐的出现及其定义
“缘坐”的记载比之连坐出现较晚,至北魏时期“缘坐”一词才见诸史籍。《魏书》载“及(崔)浩被诛,卢遐后妻,宝兴从母也,缘坐没官。”这一案件中案犯亲属缘坐没官,显然属于亲属株连。唐代也是缘坐法走向完善的时期,《唐律疏议》中的“缘坐”基本上是对指对与案犯有亲属关系的人员进行株连,如:“即缘坐家口,虽已配没,罪人得免者,亦免。”
现代对缘坐的定义往往关注其中的亲属株连。《中国古代法学辞典》中对“缘坐”的解释为:“一人犯罪而株连其亲属的刑罚。凡犯谋反等重罪,亲属一般都问斩,或没官为奴,判处流刑,且要没收家产。”由此可见,古今对“缘坐”的阐释基本上立足于家属亲族的株连。但从以上辞书的定义来看,“连坐”与“缘坐”是否同义或具有包含关系仍需探讨。
连坐与缘坐是否同义“连坐”与“缘坐”的定义历来存在争议,古今阐释有所不同。对于“连坐”与“缘坐”是否同义,学界有“二者异义说”及“二者同义说”两种观点。戴炎辉持“二者异义说”,“唐律以来,缘坐指正犯的亲属或家属亦被处罚,而连坐乃正犯的同职或伍保负连带责任。”陈顾远持“二者同义说”,认为“因他人之犯罪而得罪,称曰缘坐,又称曰连坐。”由此可见,“连坐”与“缘坐”是否同义仍存在分歧。不可否认的是,“连坐”与“缘坐”二法在唐律中相区分,有着明确的差异,王娟指出:“缘坐已逐渐与连坐、族刑等表示株连的词汇分离并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特点”。尽管唐律非常完善,但并不意味着案件的审理完全遵循法律,后世也并不一定完全继承了这种连坐与缘坐界限分明的用法习惯。金代的连坐与缘坐混淆情况比较常见,并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使研究金代“连坐”必须采用广义的“连坐”定义,将“缘坐”的内容也纳入其中。
金代连坐与缘坐的混用中国古代连坐和缘坐的研究中,金代是被忽视的一环。如陈玺和姜舟合撰的《中国古代缘坐制度考辨》一文虽然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的缘坐制度演变,但对金代的缘坐未有着墨,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金朝是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中原汉法中的连坐与缘坐均被吸收和借鉴,并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而完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连坐与缘坐混用或混淆的现象很多,使笔者开始重点审视金代连坐与缘坐的关系。金代连坐与缘坐混用之例散见于史籍中,如蒲察阿虎迭之女叉察嫁完颜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被杀后,叉察“当连坐”;金初也有“潞之军卒当缘坐者七百人”的记载。
这些均是较为明显的连坐与缘坐混用之例。不仅如此,金代还有同一案件中出现连坐与缘坐混淆的情况。大定十二年(1172),宗室完颜文谋反伏诛,世宗免除了完颜文家属的连坐。然而在晓喻其亲属时,《金史·世宗纪》记为:“汝等皆当连坐。”《金史·完颜齐传》则记为:“汝等皆当缘坐。”上述史料反映出,在金代连坐与缘坐是互通混用的,但相对来说连坐的范围更大些,基本上包括了“缘坐”。这是本文探讨金代连坐时,采用其广义定义的原因。
二、金代连坐中“族”的范围亲属
连坐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亦可称为“族刑”,其中以“族诛”的范围最广。在研究金代亲属连坐前,首先要对“族”的范围进行探析。关于中国古代“族”的范围,魏道明曾作出比较详细地界定:“三族、九族不能当三姓、九姓来理解,而应该作同姓三代、九代讲。”“明白了此节,就不难理解所谓三族、九族是以己为中心、通过对上下代数的推定来确定亲等的方法而已。”这也成为学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据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确定金代亲属连坐中“族”的范围。首先,金代存在“族”及确定亲等的方法。通过检索《金史》,可以发现很多“夷其族”、“族灭”、“族诛”的记载,这说明“族”在金代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在《金史》中还记载金显宗孝懿皇后有“惇睦九族”的美名。
另外,被视为元代杂抄宋人史籍而形成伪书的《大金国志》中记载章宗时期郑王完颜永蹈谋反,“余同逆者夷三族”。可以说明在金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如中原地区一样的把“族”按照代数确定“九族”、“三族”的亲等方法。其次,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施行连坐的“族”具体范围。大定年间,世宗对海陵党羽乌带的子孙处以停封官爵的连坐处罚,“世宗以乌带在熙宗逆党中,其子孙不合受封,停封者久之”。《归潜志》中记载王若虚劝诱刘祁为崔立撰写功德碑铭时,说:“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触其锋,祸及亲族,何以为智,子熟思之”。崔立是金末叛臣,其行为素为士林所不耻,为免留下污名,刘祁百般推脱,不愿为崔立撰写功德碑文。但王若虚以群体利益、孝亲思想和家族存亡作为劝诱手段,迫使刘祁参与碑文的撰写。上述案例中的祖母、母亲、子孙辈均是五族之内的亲属,这是金代亲属连坐中株连最远的情况。
另外,正隆六年(1161),海陵王“并诛灭萧秃剌、萧赜、萧怀忠家”,可见萧赜受到族诛。然而大定二年(1162)八月,“免齐国妃、韩王亨、枢密忽土、留守赜等家亲属在宫籍者”。海陵以族诛之刑处死了萧赜及其部分亲属,并将相当数量的剩余亲属籍没为奴,这说明金代的族诛之刑并非将主犯的亲属斩尽杀绝。综上,根据现有史料和具体的案例,可以说明金代社会中也存在以代数确定亲等的习惯,但在“族刑”的具体施行范围上,远没有达到株连九族,应以“夷三族”较为恰当。
三、金代连坐与“知情”
在中国古代,连坐者对主犯的犯罪行为是否“知情”,影响着量刑甚至连坐的施行,这是历代连坐施行的共同特点。《唐律疏议》载“若同职有私,连坐之官不知情者,以失论。”指职官连坐中,对不知情的连坐者减轻量刑。辽代承天后萧绰执政时,颁布了“兄弟不知情免连坐法令”,规定“虽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连坐”。即在对主犯犯罪行为不知情的前提下,被连坐者可以完全免除刑罚。这条法令在辽代法律制度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前辈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在金代,连坐者对主犯的犯罪行为是否知情,同样对量刑有着重要影响。
结语
天兴元年(1232),故丞相仆散端之孙忙押门,在宴饮中借故离席并北投蒙古。事发后,同饮者及忙押门亲属均遭审讯,“时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处之”。刑部郎中赵楠审理此案,发现连坐者对忙押门的犯罪行为确不知情,“遂以不知情奏”。在奏报上达之前,哀宗已作出连坐者不知情的判断,得到赵楠的奏报后,“立命赦出之”。在此案中,连坐者对忙押门的犯罪行为不知情,直接决定了审判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