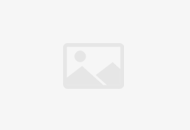大卫·帕拉丁(David Paladin,1926—1984)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印第安裔画家,他的人生充满坎坷与坚忍,还有天大的巧合和难解的神秘,有如传奇,在二战后的70多年里激发了很多人的想像力。

她说的就是帕拉丁讲给传记作家麦思(Caroline Myss)的人生经历。麦克道威尔说,“我在专业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到,之后几星期,我把他的传奇讲给每个人听——我的意思是,每一个人。”
帕拉丁讲述了自己幼年在纳瓦霍族人保留地的生活,在二次大战中服兵役时的救命巧合,还讲了他作为战俘忍受的折磨。最神秘难解的部分是,已故俄罗斯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的灵魂可能进入了他的身体并待在那里。轮回转世研究者巴纳吉(H.N. Banerjee)研究了他的案例,将其写进了《曾经和将来的人生》(The Once and Future Life)一书。
下面关于帕拉丁生平的记述,来自麦思撰著的《精神解剖》(Anatomy of the Spirit)和班纳吉的研究报告。
帕拉丁11岁时染上了酒瘾,过了几年,他离开保留地,在一艘商船上找了一份工作。在船上他和一个叫凯克(Ted Keck)的德国青年成了好友,还开始发展画画的爱好。
二战时他应征入伍,作为间谍被派往纳粹战线后方。他用印第安语传讯息,这样一旦被截获,内容仍难以破解。不幸的是,帕拉丁被纳粹抓到了。
在监狱里,他承受了折磨和酷刑,包括双脚被钉在地板上,之后,作为“次等民族”的他被送上了开往灭绝营的火车。一个纳粹士兵用步枪从背后刺了他一下,他转身一看,发现那正是凯克。
凯克将帕拉丁转移到了战俘营而不是灭绝营,使得他幸免于难,但战俘营条件非常恶劣,当得胜的盟军进驻时,发现枯瘦的帕拉丁陷入了昏迷,已奄奄一息。
而他活过来之后,说的是俄语。盟军带他去见俄罗斯人,不过他后来得以用英语说出名字、军衔和编号,于是被送回了美国军营。
战争结束后,他在密歇根医院昏迷了两年。醒来时他告诉一位护士,“我是个艺术家。”
帕拉丁回到了保留地,部落的长老们从他身体的疾病背后看到了精神方面的问题,于是采取了严厉的做法。他们把他的腿箍取下来,然后把他扔进河里。
长老们发令了:“大卫,召回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不在你身体里。如果你召不回你的灵魂,我们会让你走。没有灵魂,任何人都无法过活,你的灵魂就是你的力量。”
帕拉丁回忆说,“这比忍受双脚钉在地板上更难过。我看到那些纳粹士兵的脸,我在狱中待了那么久,我知道我必须放下愤怒和仇恨。我在水中拼命挣扎,而我祈祷的却是让愤怒离开我的身体。我只为此祈祷,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帕拉丁终于康复了。他发展了自己的艺术技能,画风和1944年故去的俄罗斯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非常相似。
印度拉贾斯坦邦大学的巴纳吉博士专注于研究印度和美国的轮回转世案例。他调查的一些案例被收入了已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著名转世研究者伊恩·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博士的著作。巴纳吉发现,帕拉丁的案例很不寻常。
与亡者灵魂转世为新生命不同,帕拉丁的情况或许是这样:在战俘营昏迷期间,他的主意识离开身体,可能有个亡魂趁虚而入。在催眠状态下,帕拉丁能讲俄语,而且还很熟悉康定斯基的生活细节。尽管他以康定斯基的风格绘画,但他也发展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班纳吉觉得,帕拉丁已经恢复了自己的意识,但康定斯基的灵魂毕竟进入过、也影响了他。
班纳吉注意到,尽管帕拉丁作画时精神很松懈,似乎在汲取灵感,但他完全还是“自己当家”,并非被康定斯基附身。
帕拉丁于1986年去世,他在《画梦》(Painting the Dream)一书中这样描绘自己的作画状态:
“我的思想是放松的,焦点模糊不清,意识处于白日梦的模式中。对脑海中变换的图象,我是有意识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浮现很像‘书写’的图形。康定斯基的几何形式给人一种秩序感、某种共鸣,就像一种语言。头脑中‘书写’的形也是一种语言。”
“我认为康定斯基和我正在绘制宇宙结构,正融入集体意识,我们俩都以独特的方式讲述故事、看待现实。”
上一篇:亚洲棕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