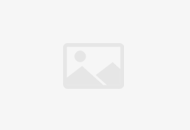这些士族把持了高级官职,但他们却有一个先天的大缺陷,那就是不能干活。这是一个很符合逻辑的结果:士族子弟养尊处优,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捞个官当,长此以往,如何能有动力好好工作?有业务能力的人也不是没有,但作为一个整体,士族官员是彻底的不称职。
这些士族子弟热衷的是做名士,而不是当能员。他们习惯于拿个麈尾,摇头晃脑地谈论老庄玄学,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前阅读统计数字。他们没完没了地谈天论地,没完没了地灌酒,不干正经事。本来他们愿意酗酒、穷嚼蛆,这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对社会并无大碍,但是这些货色霸占了高级政府职位。将政务交托给他们处理,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比如晋朝的名士毕卓,他出身士族,在西晋混了个吏部的郎官干,可是他唯一乐于投身的事业就是喝酒,因为喝酒耽误公事那是常事。一个邻居酿了酒,他居然晚上跑去偷喝,喝得正高兴,让人家的家丁抓了个现行,一根绳子捆在那里,到了天亮,一看居然是芳邻毕郎官,赶紧把他给放了。他公开宣称自己的理想是“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这样一个酒鬼怎能干好公务?可是该酒鬼的仕途居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在东晋接着当干部,还成了平南将军温峤的秘书长。无法想象这样一个立志在酒船中拍浮一生的货色能给上级提供什么帮助。
许多士族名流并非庸才,他们家学渊源,文化水准相当高,但他们更适合混沙龙、搞艺术,而不是去议事厅开会。比如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之子,极为擅长书法和绘画,天资卓异,绝非庸人所能及。但他就像大多数士族子弟一样,可能适合做很多事情,但就是不适合当官。不过他出身琅邪王家,按照特权当然能弄个官当,于是他就成了重臣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相当于骑兵参谋官。可他倒好,天天蓬头乱发,不干正事,就像现在大公司里,所有员工都西装领带,可是某个部门经理自己倒天天穿个大花裤衩子,到班上胡混,还没人敢管他。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当然可以断定,这样的公司一定存在着重大的问题,晋朝各级部门就像这样的公司。
王徽之胡混得实在是太出格了,一把手桓冲有一天故意问他:“你是管什么的?”王徽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不知道。不过有的时候看见有人在我面前牵着马走,可能我是管马的吧?”桓冲脾气很好,没有骂他是头猪,反而进一步追问:“你管多少匹马?”王徽之说:“Goodquestion!不过我从来不打听这个,怎么知道有多少马呢?”桓冲又问:“那最近死了多少匹马你知道吗?”王徽之觉得他的问题很愚蠢,说:“我连活马都不知道有多少,怎么知道死马有多少呢?”王徽之转的这些回答都有出典,这也是高级文化人喜欢的游戏之一,结合了智力竞赛和特务对暗号的特点—典籍里的话当平常对话应出来,尤其是说话时不假思索,意思还贴谱,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都能感到两腋生风,头上隐隐有光环闪动。闲话少叙,桓冲碰到这样满嘴暗号、放手渎职的下属,按理说应该革职拿办才对,可是桓冲没有勇气仅仅因为渎职就拿办一个士族。他对王徽之好言相劝:“你在单位时间很长,也是个老同志了。你看能不能好好料理料理公事?”王徽之也不理他,估计是觉得他庸俗,自顾自地抬头看天,忽然说道:“西山早晨的气息,真是让人爽啊!”像王徽之这样的混账官,就因为他是琅邪王家的人,长官反倒不敢来寻趁,居然还能升官,做到了黄门侍郎。
自古以来的文化人说起才子,都是万分钦慕,要是才子做不了大官,都说是官府没长眼。比如擅长填词的柳永,皇帝认为他只适合填词,拒绝给他官做,后来就有人抱怨说那个皇帝摧残文化,仿佛栽培文化就等于给文化人官做。很多人酗酒成性、不务正业,也被一律附会为因“无法实现理想抱负”、“报国无门”而产生的苦闷心情,也许确有此例,但在我看来,更多的“骚人”根本就不是报国无门才去喝酒,他们就是简简单单的酒鬼而已。他们不务正业,也不是因为没有条件让他们施展才能,不过是因为他们游手好闲惯了。晋朝官员中,才子比例很可能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但社会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大好处。文化和政治本是社会中两支彼此激荡的力量,两者的合流不过导致了变态的社会结构。
王源因为跟一个门第较低的人成了亲家,就把官给丢了,且永不叙用,王徽之自顾到西山去爽,连手底下有多少马都不知道,却能被提拔。那么,大家何必去干工作呢?事实上,士族确实以干具体工作为耻。用柏杨的话来说,晋朝的“行政官员以不过问行政实务为荣,地方官员以不过问人民疾苦为荣,法官以不过问诉讼为荣,将领以不过问军事为荣”。
东晋的一个官员熊远在奏章里也描写过当时的士族风气:“当今的官场把处理公务当成庸俗,把恪守法律当成苛刻,把待人有礼当成谄谀,把游手好闲当成高妙,把放荡无行当成通达,把傲慢无礼当成风雅。”王徽之就是这样一个高妙、通达、风雅的官员,他不庸俗、不苛刻、不谄谀,他的那些马死光了他都未必知道!
士族生出这样的风气,在我们看来,实在是不可理喻,但是这背后自有它的逻辑,我们将其简单归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玄学风尚,是远远不够的。试想,士族依靠门第得到官职,如果让他们去认真处理公务、执行法律,就等于把他们和寒族官员放到同一考核标准上。这些寒族能在对他们大大不利的情况下博个功名,其平均政治才能必定在士族之上,一个没有淘汰机制,一个有淘汰机制,运行下来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果用同一标准来考核的话,士族官员的愚蠢无能必定昭然若揭,所以一定要打造另一个标准,这样才能彻底地、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为“秀木”,对方为“小人”。在这个标准下,寒族的无能是无能,士族的无能就变成了风雅。
另一方面,既然只有寒族才需要认真工作,时间长了,认真工作就和下贱有了某种隐隐然的联系。这就好比只有穷人才去干体力活,所以很多中国人就留长指甲,表示自己不需要动手,是个上等人。
《世说新语》里记录了一个故事:有一次王、刘这两个人似乎很喜欢结伴和一个叫支道林的和尚一起去拜访骠骑将军何充。何充正在那里专心处理文书,见他们来了,没有理睬,接着看文书。王对何充说:“我们今天拜访你,你就别埋头于那些日常俗务,大家一起谈谈精微玄妙的话,岂不美哉?怎么还费劲看这些文书呢?”何充硬邦邦地回答说:“我不看这些文书,你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存活下来呢?”
士族发现自己只喜欢俸禄和特权,不喜欢文书之后,就把政府官职分成两类:清官和浊官。士族们“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就是说,文书看都不看就拿来签署,这样的工作就是清贵,需要勤勉谨慎的工作则留给下流胚们来干。
笼而统之地说,“清官”们的工作大抵是坐办公室,愿来就来,愿走就走。上班了也不用怎么干活,抄个手到各个办公室串个门、聊个天、谈谈艺术、谈谈价值观。下属拿来了文件,他们就在上头胡乱签个字,然后领的薪水高得出奇,还可以利用特权投机倒把、圈占土地。
显而易见,许多重要的工作没法交给这些清官们处理,比如军事。开始的时候,士族们还有领兵作战的能力,比如淝水之战中,晋军的指挥官就是谢家子弟。士族之所以能在东晋获得压倒性胜利,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握有军权。初期晋朝的军队多由士族出身的官员节制,但即便在当时,领军作战也多被认为是粗鄙的事情,比起聊天辩论来,实在是太庸俗了。祖上出过军事长官的家族,被人称为“将种”,此称呼绝非褒义。
晋朝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炎,有一个姓胡的妃妾,其父是有名的将军。有一次,司马炎和她玩投壶的游戏—所谓投壶,就是拿箭往一个壶里面投。这位妃子和他抢一支箭,把司马炎的手指头弄伤了。司马炎很生气,说:“你真是个将种!”这位妃子回道:“某些人的祖上北伐公孙渊,西抗诸葛亮指司马炎的爷爷司马懿,他不是将种是什么?”司马炎当下就被说得很羞愧。司马懿率军征讨四方,战功显赫,孙子却为此而羞耻。
发展到后来,士族能带兵打仗的越来越少,指挥权逐渐落入士伍出身的北府军将领手中。士族和军权的渐渐剥离,已经预示了士族衰败的命运。他们在此形势之下,只能加倍努力地鄙视“将种”,把自己的无能装点成一种高贵的姿态。那些军官确实也为自己的污浊而自卑,皇帝如果想对军官施加恩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武职转为“清官”,哪怕在品级上降低了,该军官也会感激不尽。
不仅军职,其他重要的职位也慢慢滑出士族之手。比如担负检察重任的侍御史,是格外要紧的职位,但是士族嫌工作量太大,不够清贵,任由它落入寒族之手。至于参赞机要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之类能参与政权枢纽的管理工作的职位,也被寒族渐次占据。士族既想清闲,又想控制权力,这两者之间必然有巨大矛盾。
士族握有最高权力、垄断高级官职的时候,就把竞争机制从士族阶层里取消了。如果动物不需要奔跑捕食就可以得到充足食物,那么捕食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弱,这些士族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得到官职,他们的政治能力也就必然逐渐弱化,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南朝的颜之推对江南的士族如此评价:“他们对人情世故完全不懂,做官不管事,也确实管不了。只会穿博衣大带,用香料薰染衣服,涂脂抹粉,出门坐车轿,走路还要人扶着,官员骑马甚至会被人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嘶鸣跳跃,大惊失色,对人道:‘这分明是老虎,你们怎么能亏心说它是马呢?’碰上了动乱,这些雅致至极的士人肉柔骨脆,体瘦气弱,路也走不得,凉也受不得,唯一能干的就是穿着绮罗绸缎,怀揣金银珠宝,在路边等着饿死。”
从马上征战的司马懿到不知道马数的王徽之,再到指马为虎的王复,展现了士族的衰落轨迹。
士族子弟这种先天缺陷,给皇权复兴铺平了道路。他们霸占了高级职位,却又把实际工作留给了低级职位,这就等于给皇帝开了个后门,皇帝可以借此培植属于自己的力量。虽然皇帝没有办法把他们从政府里清除掉,但是可以把这些懒胚架空。无所事事的“清官”虽然地位尊崇、待遇优渥,但他们离真正的权力核心越来越远。晋朝是唯一一个士族享有崇高地位,又握有实际权力的王朝。南朝的寒族开始颠覆士族的统治,这些寒族的官职品级很低,但却握有实际权力,士族对此处于无力反抗的地位。“你想管?行啊。先把这些案卷都处理了!嗯,也不多,一天看八个小时就够了。”这些士族就会马上傻眼。
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留给士族的最终只有空洞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