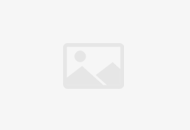猴年来临,比起刚刚过去的不知到底是“山羊年”还是“绵羊年”的羊年,猴年带来了新的难题,那就是这种近似人的灵长目动物在汉语中到底有多少种叫法。
“马骝”是什么东西?
看马戏是中国人民热衷的娱乐活动,不过虽说是“马戏”,但在实践中,马戏团很少有以“马”作为主角的。相反,猴子才是所有马戏团必不可少的配置。相对马而言,猴子虽然调皮,但是领悟力高,占用空间少,喂养成本还低。不少耍猴人甚至可以用个体经营的方式耍猴。
街头耍猴是中国一景
很不公平的是,厥功甚伟的猴子竟然被马抢了风头,“猴戏”被叫成了“马戏”,不过猴子们也不必过于沮丧,毕竟“马戏”其实可以歪解为指“猴”的。
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把这种和自己相貌相似的哺乳动物称之为“猴”,江浙地区也将其称为猢狲(或其变音“活狲”)。但在遥远的岭南,猴子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马骝”,猴子们大可把“马戏”解为“马骝戏”。
“马骝”这个怪名是如何出现的呢?
现在的广东在历史上居住着大量讲侗台语的壮人、俚人,因此粤语中不乏来自壮语的词汇。北方说的“荸荠”在广州被称作“马蹄”。近年随着广式甜品、饮料凉茶在全国范围内风行,“马蹄”之名也为很多两广之外的人熟知。
“马蹄”的得名有说法认为是因为荸荠形似马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凡是见过荸荠的人都应该觉得要把这东西和马蹄联想在一起需要有非同一般的想象力。而在福建的闽南地区,荸荠被称作“马荠”,更说明形似马蹄的说法不可信。
其实“马蹄”的说法和百越先民有莫大的关系。今天的壮语把“果”称作maak,而壮语普遍把修饰成分放在中心语后,于是李子就是maakman,桃子是maaktaau,梨是maaklai,龙眼是maakngaan,葡萄是maakit,橘子是maakkaam。
所以广东福建的“马蹄”和“马荠”相当有可能是某种果的意思,“马蹄”的“蹄”可能是“地”的意思,“荠”则像汉语自己的词语,“马蹄”为“地果”命名法颇似上海的“地梨”。虽然两地现在都说汉语,不过先民说的语言仍然留下了痕迹。
荸荠是常见的水生食用植物
那么“马骝”是否也是类似情况呢?
其实不然,马骝不似马蹄、马荠有较为可信的壮语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上“马骝”的分布并不限于南方,而是一个通行大江南北的词汇。
宋朝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写道“北人谚语曰胡孙为马流”。所谓“马流”,自然跟“马骝”不过是一个词的两种写法。同样,“胡孙”自然也就是“猢狲”。可饶有趣味的是,在赵彦卫看来,“马流”非但不是岭南的特色词汇,反而是“北人谚语”。《西游记》中“马流”也有出场——除了“泼猴”之外,第十五回孙悟空还被菩萨娘娘大骂“我把你这个大胆的马流,村愚的赤尻”!自然,“马流”和“赤尻”都是猴子的意思。众所周知,作者吴承恩也并非岭南人。
《西游记》中的观音娘娘爆粗是家常便饭
马骝还是猱?
马骝到底是什么来历呢?
上古典籍中的“猴”字并不常见,单独出现更是难觅踪影。《诗经》里面有一次提到猴子,但是出现的字为“猱”,见于《诗经·小雅·角弓》第六章“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微猷,小人与属”句。根据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注解:“猱,猕猴也,楚人谓之沐猴,老者为玃,长臂者为猿,猿之白者为獑胡,獑胡猿骏捷于猕猴,其鸣嗷嗷而悲。”
对现今的中国人来说,猱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生僻字,比猴罕见得多。中古以降,猴一直是该种动物较常用的名字。但奇怪的是,汉语亲属语言中能和“猴”对上的很少,反倒是“猱”有大把的“亲戚”。
“猱”的中古和现代汉语声母都是n,但是它的声旁却是“矛”,因此上古汉语中这个字的读音为ml'uu。这个词历史极为悠久,在商朝甲骨文中即出现了“夒”,形状近似猴子的侧面。此外,“獶”也是“猱”的另一种上古写法,见于《礼记》“獶杂子女”。
甲骨文“夒”的字形
在汉语的亲属语言中,也不乏和上古汉语“猱”字读音相近,表示猴子的词。
缅文中猴为myok,彝语则是anyu,西夏语用“摩”来对音。都说明这个词是古老的汉藏语系同源词。而“马骝”则不过是这个词的一种缓读形式而已了。上古以后“猱”本身渐渐退出口语,但留下了“马流”这个残迹。不明就里的后人因此以为猴可御马,故有“马留”等说法,其实和“马蹄”一样,都是望文生义了。
有趣的是,后来“马流”的意思还扩大了,《云麓漫钞》中还有“马文渊立两桐柱于林邑,岸北有遣兵家十余家。不反,居寿冷岸南而对桐柱。悉姓马,自相婚姻,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的记载。尽管这里名义上是说那些人因流寓而又姓马才叫“马流”,实则大抵和中国人如今蔑称东南亚人为“马来猴子”差不多性质。
沐猴而冠的都是母猴?
既然如此,“猴”在上古时期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否上古人只知有“猱”而不知有“猴”呢?
前面提到上古时期的“猴”不太单独出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上古时期没有“猴”这个字了。只是“猴”一般和其他字结伴出现。
《说文解字》中,多有以“母猴”来解其他表示猴子的字的做法,“玃”、“夒”、“禺”等字都可解作“母猴”。《韩非子》中,燕王被一个卫人以“能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的神技欺骗。而《吕氏春秋》中则有如下总结:“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
猴子当然不可能都是母的,而在荆棘末端雕只猴子也不必强调非要是母的,母猴也并不比公猴更加像人,所以这里“母猴”并不是指母的猴子,而是指这个物种本身。
其实“母猴”还有“猕猴”、“沐猴”的写法。这些写法出现都很早,《楚辞·招隐士》中就有“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史记·项羽本纪》更是有著名的“沐猴而冠”的故事。
综合来看,不管是“母”、“猕”、“沐”,应该都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词头。只是后来语言发生了进一步的演化,词头终于被丢掉。“猴”也就粉墨登场了。
另有一个表示猴子的词“禺”则是“母猴”分化出的不同变体而已——上古汉语“猴”为goo,“禺”则是ngo,差别并不大,而且后者很可能是受到m词头的作用,声母鼻音化了。
广州首县叫做“番禺”,不过这个番禺和猴子有没有关系很难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云麓漫钞》中,通语中的猴子称为“胡孙”,“马流”是作为和通用的“胡孙”相对的方言词汇出现。“胡孙”实际就是“猴孙”,有时也作“王孙”。唐朝大文人柳宗元还曾经专门作《憎王孙文》历数猴子品行之恶劣,甚至发出“然则物之甚可憎,莫王孙若也”的感慨。
“猿”和“猴”是什么关系
只是上面说了半天,也并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猴”的词源究竟如何?
可能看一看汉语中其他动物的命名会带来些启发。
汉语中有“犬”、“狗”之分,一般认为其区别在于大小,犬大狗小。从上古汉语的语音来看,狗为koo’,犬为khween。表示小马的“驹”则是ko。韵母也为o,即所谓上古汉语的“侯部”。
很巧的是,“猴”也是一个这样的词,以g为声母,oo为韵母,不得不让人生疑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指小的词汇。
假使“猴”真的指小猴的话,那什么词指大猴呢?
凑巧的是,汉语中还真有一个和“猴”语音结构较为相似,又指大型动物的词——“猿”。
“猿”在汉语亲属语言中的出现频率远不如“猱”,但也并非全然不见,景颇语中猴为woi/we,西夏语中则有wj?,皆似汉语的“猿”。
而在汉语自身,“猿”出现得也相当早。《山海经》里就有“发爽之山,无草木,多水,多白猿”。《吕氏春秋》中则有著名的神射手养由基射白猿的故事。此外,猿有时也以“蝯”、“猨”的字形出现。
现代生物学里的“猿”和“猴”分得相当清楚,类人猿包括长臂猿、红猩猩、倭黑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相比猴子,猿跟人在进化上更加接近,而且都没有尾巴,但古人则只能依靠体形大小来区分。《玉篇》对猿的定义是“似猕猴而大,能啸”。中国历史上的猿主要是长臂猿,相比大猩猩、黑猩猩之流也确实更像猕猴。
长臂猿是中国目前仅有的猿类
只是猿比猴要幸运得多,在中国人鄙视猴的各种卑劣品行的同时,猿作为长寿灵兽,则多被嘉许。猿的叫声也被认为是“哀鸣清绝”。三峡猿鸣更是诗词讴歌的对象,如“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更是被赋予了人性,如《搜神记》《世说新语》中各有一则小猿被抓,母猿哀号许久,最后肝肠寸断而死的故事。当然猿作为灵兽,故事中害死它的人也没好下场,《搜神记》中“未半年,其家疫病,灭门”,《世说新语》里此事被上司听说后当事人被黜。
可惜的是,中古以后通人性的猿由于对环境要求较高,分布范围越来越窄,三峡猿鸣已成过往。因此猿已经不为人熟悉,和猴多有混淆。明朝《三才图会》中,猿甚至长了尾巴,充分说明猿已经近乎一种传说中的动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