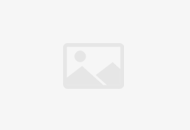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放光芒的太阳”图标都是用来表示地理高点的,但是很奇怪的是有很多“放光芒的太阳”图标都标注在山坡上,有的甚至位于沟底。
考古人员贺青海经过长达9年的调查考证,在陕北发现秦代的星台群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命令驻守上郡的大将蒙恬历时6年主持修造了一个以陕北榆林为中心的"地上天国"星台群。”陕西省榆林市考古人员贺青海在11月中旬对外宣布,这个星台群遗址是他的研究团队经过长达9年的调查考证之后发现的,该星台群总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对秦始皇时修建的“高速公路”——秦直道的研究,星台遗址的发现应该是我在研究秦直道后的意外收获。我手中一份1976年测绘、1980年出版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对这份军用地图的研究、并对上面的一些标志进行实地考证,发现了秦帝国星台群的秘密。”贺青海告诉记者。
在研究秦直道烽火台时,贺青海发现他手中的这份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对秦帝国的烽火台都有标注,是用“放光芒的太阳”这样一种标记来表示的。“烽火台遗址都是秦直道附近的制高点,这个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很正常,也是军用地图的常规做法。我们在地图上标志的指引下,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烽火台遗址。”

一次偶然的机会,贺青海在观察军用地图时发现有一处区域有七个“放光芒的太阳”的标志恰似天上北斗七星星座的标志,在实地考察以后他得到了同样的答案。贺青海恍然大悟,他终于找到了研究这些土台子的思路。这些众多不知用处的土台子是不是和天上的星宿有关?
研究发现星象台与天空的星宿存在对应关系,总体轮廓为女娲补天形状
从2000年以来,在千山万壑之间,贺青海像一个苦行僧,时常打着绑腿,背着行囊独自一人或者和他的考察队伍出没在荒山野岭之上,到现在为止,走了陕北黄土高原的多少沟沟岭岭,他自己也记不清。“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和军用地图对比相结合的方式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土台子都和天上的星宿有关,并且都是很有规律地进行分布。”贺青海说。
“通过实地考察和推算,我们发现共有1424个星象台与天空332个星宿或星官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地上为什么是1424个星象台我们有推算办法,通过考察和分析发现这些星象台对应着秦帝国时的332个星宿或星官,比如天狼星是单颗,北斗七星是多颗,这些星数加起来就可以得到1424颗星,由于和地面的星象台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正好得出是1424个星象台。”贺青海说。
这1424个在山顶、山坡甚至沟底夯筑或铲削成圆形或椭圆形的用来观星、祭星、占星的星象台,以陕西榆林为中心,广泛分布在陕西省的榆林、延安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三市共14个县(区)、旗中。它们东临黄河,西跨明长城内外,南至秀延河下游,北达鄂尔多斯高原东北角,占地面积达到2.8万平方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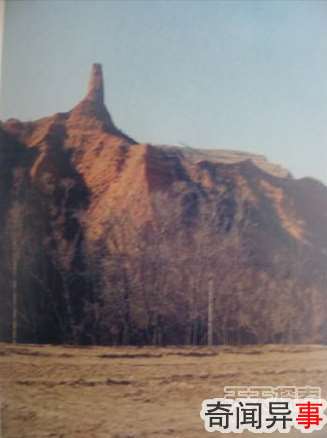
“‘九五之尊’在古代是帝王的代称,因此女娲的身高与体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在实地考察中还发现女娲形"地上天国"星台群自下而上共分九层。每层各有其名,各含有不同的若干星宿或星官,这不仅印证了‘天有九层’的古老传说,也表明当时中国古代的宇宙学说——盖天说仍占据统治地位。”贺青海告诉记者,女娲补天型星台群的认定和其象征意义的判定并不是凭空妄断。在他们的考证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女娲补天型星台群就已经存在了。
专家认为,秦朝有建"地上天国"星台群的可能,但该研究仍存在一些疑点
目前,贺青海他们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一些权威的认定,其编撰的《秦帝国全天星台遗址及其源流考》一书在经过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科学院相关专家主持的专家评审组评审以后,11月已由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陈美东研究员认为,秦星台是秦长城、秦直道之后的又一庞大而周密的建筑工程,在中国建筑史上也应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贺青海等人的考证也留下了一系列的疑问。记者查阅了一些相关历史材料,并没有发现蒙恬修建秦始皇“地上天国”星台群的任何史料。中国两位秦汉史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对记者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看法。

“秦朝时,中国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天文学观念。1977年,湖北发掘出一座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考古人员发现在一只漆箱的盖面上绘有一幅彩色天文图,并且上面已经标有二十八宿的名称。后经科学测定曾侯乙墓的年代为公元前433年左右,这表明在公元前5世纪初或者更早,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
“从秦朝当时的天文水平和其他科技发展条件来说,秦朝有建‘地上天国’星台群的可能,很多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秦朝的都城咸阳的宫殿都和天上的星辰有对应的关系。当时陕西的渭水被当成了天上的银河,而渭河两岸的一些宫殿包括渭河北岸咸阳宫、渭河南岸的兴乐宫都和天上的星宿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秦汉史研究专家徐卫民教授说。

陕西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前任会长周天游教授表示:“贺青海从天文学的角度进行的一些考察和研究可以弥补我们的很多不足,虽然他的研究成果只是一家之言,目前也还有很多不足,但是这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角度,不管他的研究结果究竟是对还是错,他现在对中国秦汉史的研究方面发出的都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