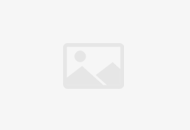悔婚是因为信守前诺?
老夫人在张生退敌之后,安排了一场筵席,大家都以为她要践诺,把崔莺莺嫁给张生。但就在这场筵席上,老夫人在张生和崔莺莺刚刚见面后,就发令了:“小姐近前,拜了哥哥!”大家吃了一惊。老夫人还让崔莺莺给“哥哥”张生把盏,崔莺莺满心的不情愿。而张生更是气极,以“小生量窄”为由拒绝了。而夫人不识趣,又强行要求崔莺莺再敬一杯酒。
她似乎不把局面弄糟就不满意。
我们来看一看,老夫人为什么要反悔,为什么要出尔反尔?
说老夫人不肯让女儿嫁给张生是嫌贫爱富,这个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崔家是已故相国一家,然而家业凋散,身边只有伶仃数人陪同了,出场介绍时,连崔莺莺身边的小丫鬟红娘都介绍一番,实在是数百人里只剩三四口了。而张生,也是礼部尚书之子,虽然人丁单薄,但与崔家情形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而郑恒又是什么特别有权有势的货色吗?郑恒虽是郑尚书之子,可也是父母双亡。张生与郑恒,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又值得什么扬此弃彼吗?
第一种可能是崔莺莺已许给了郑恒,老夫人要信守前诺。老夫人回答张生的质疑时说:“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即日有书赴京唤去了,未见来。如若此子至, 其事将如之何?”
其实,老夫人如果守了张生的诺,势必要背弃郑恒之诺;守了郑恒的诺,就要背弃张生之诺。而郑恒是其内侄,老夫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老夫人对张生赖婚,虽然是背信弃义,但是这种行为也是有当时的法律依据的。中国古代社会对悔婚以及悔婚易嫁是严厉禁止的。唐代,在《唐律疏议卷·户婚》里说:“(女方悔婚)杖六十,婚如约”;女方“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女追归前夫”。元代,《元史·刑法志·户婚》里说:女方“悔(婚)者,笞三十七;更许他人者,笞四十七;已成婚者,五十七。女归前夫”。法律规定如此严格,老夫人怎敢轻举妄动?
本来,答应崔莺莺许配张生,也是孙飞虎围寺时事急从权的无奈办法。崔莺莺已有婚约,如果再许他人,不仅触犯当时法律,再许的婚姻也无效。
这肯定是老夫人赖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恒是高贵的白衣衙内,张生是寒门的新科状元
我一度以为,除了宥于法律之外,老夫人因为郑恒是自己的内侄,才导致了偏心,想到肥水不流外人田。但发现这种设想经不起推敲。这种亲上作亲,金、元两代是忌讳的,中表不能成婚,是当时的禁令,至明代洪武年间才解禁。再说了,郑恒与崔莺莺,也只是长辈口头允诺,不曾“执羔雁邀媒”,也就是不曾下聘,真要翻起脸来,查无实据,法律也奈她们不何。可以说,当时法令指出的“悔婚杖六十”是打不到崔莺莺身上的。
显然,老夫人并不是仅为了信守前诺而悔亲。
值得注意的是,老夫人对张生的第二次赖婚,是发生在张生中了状元、封了官之后;而且还有白马将军杜确的撑腰。而郑恒,除了挂一个尚书之后的名头,是一位既无权又无势的白衣衙内,老夫人却没有向郑恒提出状元及第之类的要求。如果嫌贫爱富,恰恰应当舍郑恒而取张生。
我推测,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老夫人的选择与门阀制度有关。《隋唐嘉话》载:“高宗朝,太原王、范阳卢、萦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望族,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于是不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高宗显庆四年,曾下令禁止“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娶。可是越是禁止,他们越怕贬低门阀,抗拒禁令,自为婚娶。这一点我在后文将有更详细的描写。而博陵崔与萦阳郑两家同系第一等的高门士族,在这个意义上,郑恒再落魄,门第也是高尚的。但姓张的就不一样,顶多也就是“近代新门”。在唐代,高门士族嫌弃皇族门第低,连皇亲都不愿嫁的例子是有的。是以,崔母不同意把女儿嫁给一个新科状元,而要把女儿嫁给一个白衣衙内,在当时也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有理由却不等于正确。老夫人放着张生这样一个身份相配、前途无量的新科状元不要,却偏找一个无德无能的小瘪三做女婿,还违背女儿的感受,无论如何是不明智的,也是眼光短浅的。相对于女儿的聪明伶俐,这个母亲可以说是既无信用,又无谋略,甚至连基本的技巧都没有。崔莺莺表面上没有反抗,只是碍于她的母亲身份,更因为她尚且不能确定张生真心与否,是否值得她付出。一旦她与张生站在了同一阵线上,这个智商不足的母亲,也就难以成为她追求幸福的障碍了。
某种意义上说,暧昧比恋爱更有趣。老夫人给这对小两口创造的困难,是为了给他们俩寻找乐子呢。文/侯虹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