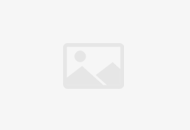父爱主义(Paternalism)又称家长主义。根据《法律哲学:百科全书》所载,它来自拉丁语pater,意思是指像父亲那样行为,或对待他人像对待孩子一样。该书又特别指出,Parentalism是家长主义在性别上的中性的表达方式。
围绕家长主义的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议至少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关于它有三个著名的例子。第一,1698年,洛克警示人们不要将“父权”与“政治权力”混淆。第二,康德同样警告,“如果一个政府建立的原则是对人们的仁慈,像父亲对他的孩子一样,换句话说,如果它是家长主义式的政府,这样的一个政府能被人想象出来的最坏的政府。”第三,在18世纪末,边沁在其《道德与立法原理》中,质疑是否应该将“事关自己的冒犯”视为刑法所要管辖的内容。当然,在这此期间,从其他角度研究家长主义的论述多种多样,有从奴隶制度着手,比较美国的奴隶制和俄罗斯的农奴制度,有从社会政策着手,认为虽然很多历史学家认为1815年到1833年的英国是个自由主义的时代,但功利主义与自由放任政治经济学的盛行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并没有影响这个阶段家长主义思想在社会政策上的重要地位,甚至有“亚里士多德家长主义理想的复兴”一说。
学界在使用家长主义概念的时候,存在着诸多分化和歧义,有的将任何带有“善意”的法律行为都归结为家长主义,有的将带有“善意”和“强制”规定的法律都归结为家长主义式的,在概括意义上使用而不加细分,更多的是将其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并予以细化。在这些再分类中,主要分为两种:软家长主义和硬家长主义。
软家长主义软家长主义的核心是:只有“真实”(即那些在认知上和意志上没有欠缺)的决定才值得尊重。软家长主义之所以被认为是“软”的,是因为它不对任何真实的决定进行干预。相反,它只对受到削弱的决定,即“强制、虚假信息、兴奋或冲动、被遮蔽的判断,推理能力不成熟或欠缺”的结果进行限制和干预。正如Feinberg所说,软家长主义保护当事人不受“不真实反映其意志的危险的选择”的危害。因此,软家长主义不是阻碍自治,而是在实际上保护和提升自治。当然,围绕软家长主义的态度争议不少,也有人认为它不是真正的限制自由的原则。
软家长主义典型的例子来自密尔,这个例子涉及一个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要过一座被毁坏、有危险的桥。密尔解释说,有人“可能抓住他把他拉回来而不真正侵害他的自由,因为存在于他想要做的事情的过程中,而他不想堕入水中”。在当事人不知道关于桥安全与否的情况下,很难说当事人是自由的或自治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过桥这一行为的真正结果是什么。
对软的或弱的家长主义证成(justify)的依据是主体缺乏必需的、做出决定的能力。在主体决定从事受限制的行为为以下行为之一时,对其的干预(intervention)可以被软家长主义证成。(1)实际上没有获悉相关信息;(2)没有充分理解;(3)被强制;(4)其他不是实质自愿的情况。总之,只有在当事人的选择在实质上是不自愿的情况下,并且是为了当事人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软家长主义才能证成这种干预。软家长主义的理论依据是:人们在做出的选择并不总能反应他们的愿望和偏好。信息的缺乏、不成熟或不自愿都能阻碍愿望的实现。因此,即便声称自己是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ist)的人士,也同意基于软家长主义而进行的规制和干预。
Thaddeus Mason Pope还提出关于软家长主义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第一,在确认软家长主义条件的时候,要强调(干预人的)动机。软家长主义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被干预者)在实质上不自愿的情况下就可以干预了。正如密尔所说,这些干预必须为提高主体的利益和自治。换句话说,软家长主义的目的必须是为了让当事人自治。干预人的动机很重要,在主要是因为当事人的利益而不违背其其实质的自愿进行干预才算是软家长主义。在当事人缺乏实质自愿与干预人的干涉之间应该存在因果联系。第二,学者们同意将软家长主义看做一个限制自由原则,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只有软家长主义才能被证成,其他的限制当事人自由的原则都不能被证成。
硬家长主义Anthony T. Kronman认为,父爱主义(家长主义)就是通过限制当事人的能力(power)去做法律认为违反他自己利益的行为来保护承诺人自己。G·Dworkin关于硬家长主义的定义是最有影响的。在其1971至1992年关于家长主义的定义中,他将条件限定在管理人与当事人当时的选择相反,对其行为进行限制和干预。Feinberg起初在其Harm to Self 中,将硬家长主义解释为国家限制“具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行为,哪怕在当事人充分选择的时候,也要违反他们的意志,使其免于伤害的后果”。十年后,在他的哲学百科全书家长主义章节中,他又将硬家长主义定义为对“充分”或“完全”自愿的自我关涉的行为进行的限制。Gert 和Culver主张应对家长主义干预予以道德上的要求,他们认为在对自由进行限制的时候,必须要证明这种限制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才能是家长主义的。他们认为需要对这种干预进行道德上的证成,而且将这一要求视为家长主义行为的“重要因素”。
Pope在总结了各种硬家长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硬家长主义的四个逻辑上的充分必要条件:第一,管理人必须主观上具有限制当事人自由的意图。第二,管理人必须限制当事人的自由,主要是因为他相信这一干预有助于提高当事人的福利。管理人必须基于善意的动机,或者增加当事人的福利,或者使其免于伤害。第三,管理的善意动机必须独立于当事人当时的偏好。否则,管理人就是为当事人提供便利的人而非限制其自由者。第四,管理人必须或者(1)不管当事人是否实质自愿地从事被限制的行为的事实,或(2)故意地限制当事人的实质自愿行为。否则,管理人的限制就是软家长主义式的。Pope认为Dworkin和Feinberg他们要求“违反”(contrary)当事人的意志进行干预过于苛刻,因而只要是“不顾”或“不管”(disregard)就行了,同时他也认为Gert 和Culver的定义中的道德要求不是价值中立的。
在此基础上,Thaddeus Mason Pope对硬家长主义进行了精致的分类。针对第一个条件:管理人必须主观上具有限制当事人自由的意图。Pope将描述管理人限制自由的方式划分为以下几种:(1)直接和间接的家长主义;(2)积极和消极的家长主义;(3)强迫和强制的家长主义;(4)即时的,溯及的和预期的家长主义。针对第二个条件:管理人必须是主要出于对当事人的善意(Benevolence)而限制其自由。Pope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善意(Benevolence)而非善果(beneficence),管理人必须有意(volens)地促进当事人的利益(bene),但不以实际上为当事人谋取到现实的利益(do (facere) good (bene))为必要。Pope根据第二个条件将硬家长主义分为:(1)混合的家长主义与非混合的家长主义;(2)纯粹的家长主义和非纯粹的家长主义。
家长主义有以下特征:
第一,家长主义目的是为了相对人的福利、需要和利益,主要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阻止他自我伤害,二是增进其利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或政府的“爱”。
第二,家长主义的措施必然是不同程度地限制相对人的自由或权利。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或政府的“强制”。法律家长主义因强制对象的不同区分为直接家长主义与间接家长主义两种情形,前者是对受益的相对人的自由的限制,比如法律要求司机系安全带;后者是对与受益者相对的主体的自由的限制,受益者不一定总是其自由受到限制的人,比如禁止把受害者的同意当作推拖法律责任的辩护理由,这一法律限制主要是影响施害者,而试图保护的却是心甘情愿的受害者。
第三,家长主义的措施在客观上亦产生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效果。法律家长主义与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和社会连带之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有些法律或政策的规定,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公共福祉,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则是家长主义的。如台湾大法官在论证第472号关于法律要求强制保险的规定是合宪的时候,就以公共福祉和社会连带作为证成该规定的理由,其立法的目的是想消除由于对当事人的伤害而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的负担。对于以公共利益取代法律家长主义的观点。
自从遭到密尔那篇享有盛誉的文章《论自由》的批判之后,法律家长主义已不为民主主义理论家及其实践者所关注。如果A在未经咨询B的情况下,为B的最大利益行事,且可能强制B服从,这种观点近来被认为只是一种“对任何种类的政府行为来说,都几乎是一种‘非美国式’的基本原理”。并由此产生了对家长主义的诸多苛责,对家长主义广泛的敌意如果说不是不可克服的话,也是很强的。以致于很多根据家长主义法律做出的判决也被故意蒙上一层非家长主义甚至反家长主义的面纱。而很多在反家长主义之名下的苛责,现在已经被抛弃。在20世纪的初叶,在自由至上主义盛行的年代,在对社会主义恐惧的年代,哪怕是为了公共福利而对妇女健康和医疗提供帮助的法律,也因为其对社会权的提升而被斥之是“社会主义”的,要被禁止,更有人将其斥之为“虚伪”。但是,家长主义的案例在美国历史上是的确存在的,而且为数不少,而它作为一种法学思潮所引发的学术讨论也持续到现在。如1963年哈特就曾表示过对家长主义的认同,他甚至承认强家长主义这一亚种,他说:“在我们的法律里,不管是刑法还是民法,有很多家长主义的例子”。
现有的资料表明,对法律家长主义的争论在方法论上集中于两个维度,一个是从法律经济学的维度进行,一个是从价值论的维度进行。
针对法律家长主义的法律经济学分析着重于效率(efficiency)和偏好(preference)。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主张自由至上,而Paul Burrows认为,对法律家长主义制度的经济分析能为国家或机构的家长主义干预提供基本原理。他提出了与以往经济分析不同的框架。传统的法律经济学框架使用的是与传统经济学理论一致的狭义的理性假设。这个假设认为,人们的偏好为了偏好的内在的一致性满足一系列的要求,Kahneman称之为理性的逻辑性概念。该假设认为人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偏好,这些偏好也是不变的,但偏好的内容与逻辑理性没有紧密的联系。逻辑理性的特点是它仅关注人们的偏好,而不以和理性行为的结果相联系。而实质理性是与人们的行为是否在追逐他们自身的利益获得成功相联系的。实质理性的概念为构建一个分析家长主义法律干预的含义的框架提供了一个起点。
他还认为,由于诸多人类选择的不可靠性,我们不应该假定(偏好-选择-评估命题提供的)自由选择的工具主义观点在各种选择背景下都具有说服力。支持自由选择的工具主义观点,和支持被初步证实了的家长主义的工具主义案例(自由选择的对立面)应该在每个特定选择背景下进行评估。一般的观点基于此前的(自由主义的)信仰对(法律和其他形式的)家长主义干预进行无条件的反对,这种理论或证据不能被证成。对家长主义法律干预的主要的反对意见是:阻止选择自由是失去一种内在的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限制阻碍了人们的消极自由。按照纯粹自由主义的观点,只要不阻碍他人,人们就有基本的自治权和自我决定权。因此,私人选择应在私人领域内,不管家长主义干预可能的工具主义价值有多大,也不管失去的消极自由有多小。而这忽视了积极自由的效果,将对人们自由的法律干预进行过分简单化了。消极自由与个人恰好能选择的选项中进行选择的范围有关;积极自由与个人恰好能选择的选项目进行选择的质量有关。在广义的自由范围内,超越个人事前明显的偏好进行的法律干预对整体自由的破坏就不再是清晰的了。即便限制了消极自由,也要看对整体的自由的影响,看看对积极自由的提高有多少。限制消极自由所失去的内在固有价值与由此扩大的积极自由的工具性效率增加的价值相冲突。这个框架承认法律家长主义的干预将在特定情形下提供一种有效率结果的前景。
尽管很多学者,包括支持家长主义的学者都认为家长主义与效率是不相容的,如波斯纳就认为要求系安全带的规制是无效率的(inefficient),但有学者通过经济分析认为不仅相容,甚至认为经济分析为家长主义提供了核心的正当化理由。也有学者在考虑家长主义的时候分析法律如何干预乃至形塑(shape)个人的选择和偏好, 并得出自由主义的家长主义并非不可能。
对家长主义批评的另一个维度来自价值论。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个人是否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真正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法律是否应保持价值中立性。一个是对于自治这一价值目标在法律中的地位。R. Dworkin的平等自由理论认为政治决定必须尽可能与任何特定的好生活或赋予生活价值的观点分开。就象Joel Feinberg所说的那样,硬家长主义“看起来意味着,国家比个人自身还清楚其利益”。这种限制自由的原则受到广泛的诅咒“因为他将关于什么是好的概念强加给人们,而人们认为这种概念是不具吸引力的”。由于美国的政治制度一定程度上拒绝一个客观上可定义的关于“好生活”的概念,自我决定的权利就成了美国最重要的价值。因此,“人们能够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他们好的东西”这一观点广为接受。所以美国人不愿赋予政府来告诉自己什么是、什么不是自己真正的利益的权威。
就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有这样的回应:对于个人选择应该被尊重,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至少比第三方代替自己做决定更好的观点,Sunstein教授认为,这种主张在实际生活没有得到支持,至少没有在这种普遍意义上得到支持。他以吸烟者、酗酒者、暴食者为例论证他们的选择不能被理性地认为是提高他们好生活的最好的方式。说他们选择的是最好的饮食,或比其他人为他们选择的饮食方式更好是一种很荒唐的说法。他们的选择不能被理性地认为是提高他们好生活的最好的方式。在这些情况下,人们的选择不能被认为是提高他们福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他们愿意花钱请人帮他们做更好的选择。Jeremy Waldron认为,中立性要求原来是针对宗教信仰的,现在被扩展到道德规范中。但是一旦中立性的范围被扩展到包括长期存在的道德,就存在着将中立性原则与道德基础切断联系的危险。由于种种原因,自由主义的中立性遭受了严厉的批评。很多批评认为这个观点不仅是似是而非,而且是内在不一致的,甚至被批评为是荒谬的。
尽管拉兹强调他拒绝(像亚里士多德所建议的那样)认为立法者必须支持一些单独的关于什么是好生活的标准,但他认为立法者和官员在立法和为社会和个人设立框架的时候可能考虑到什么是生命中好的和有价值的,什么是低级的和邪恶的。一些生活方式的确比其他的方式道德上低下,立法者的工作是不鼓励这样的方式。他认为,对个人自治能恰当地理解,立足于一个道德诉求,并与社会环境有关。
就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有这样的争论。有观点认为,自治具有基本的道德基础,个人自治并不一定会提高自己的利益,相反,有些时候自我决定会导致对自己的伤害。一般来说,一个人会通过自己决定来更好地达到自己的利益,他人不得干预,因为自治是比个人福利更重要的事情。个人的轻率对自己生活的威胁只是针对的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只属于他而非他人。仅因为这个原因,他必须自己在不直接影响他人的个人疆域里自己决定,不管结果是更好还是更坏。这种解释依据的是纯粹的个人最高权(sovereign)自治的概念,将自治视为最高(sovereign)的权利。也有观点认为自治既不是当事人自己的利益(自我实现)的派生物也不是比它更基本的概念,而是与其并列的一个概念。它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当事人被允许在关于自己的事情上能自己做出决定,他的个人利益会最可靠地深化,但是在没有告诉价值的一致性的时候,一个人必须尽力去平衡自治与个人福利之间的张力并在此之间决定,因为两者中没有一个是自动比另一个更优先的。这种妥协,没有满足自由主义者坚持的个人最高权,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哪怕是在个人疆域内也限制个人权威,但是它与一种法律家长主义是一致的,因为支持它的人能做出让步,认为家长主义的考虑在应用的时候可以作为有一定说服力的理由,即便这些理由与其他理由相冲突而且也不是决定性的。这种温和的家长主义理论允许个人自治的空间,但是并不以个人最高权的模式对待它,因为它允许将其和其他的考虑进行平衡,因此剥夺了它的最高地位。总之,自治应该不是一个非此即彼(all-or-nothing)的概念,而应是一个程度上(more or less)的概念。自治与利益的领域并非非黑即白,而是在很多灰色的阴影中。对于那些由年老、贫穷、柔弱、迷惑的人们引发的问题不能完全将其放到贴有自治标签的盒子里或帖有利益(慈善)的盒子里去。这些问题是复杂的、相关的、有条件的和暂时的。法律应采取一种程序,以允许对受益人的能力和他们所需要的帮助的多重性质进行反思。很多受益人对自治和帮助的需要兼而有之,而且程度变居不同,不是一种利益完全排除另一种。
综述家长主义制度在美国法上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本文仅对其在合同法、行政法和宪法领域的应用进行梳理,但其涉及的领域并不限于此。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某些由合同引发的但最终涉及宪法法律关系的案件,本文将把它们放在宪法部分讨论。
合同法现有的资料表明,美国最早运用法律家长主义的判决是1894年的Frisbie v. United states。1890年的《独立养老金法》规定,对于依靠养老金为生的人,任何代理人、律师等在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不得要求其超过10美元的报酬。超过该数额应经养老金专员(Pension Commissioner)同意。在该案中,一位律师向一位因丈夫在为军队服务丧生而享受养老金的寡妇要求10美元以上的报酬而被定罪。David Brewer法官在判决书中写到:“国会当然有制定限制个人订立某些合同的权力”。其后就是著名的Holden v. Hardy,尤他州的法律规定,出于对矿工的健康和安全考虑,每人每天的工作最长时间不超过10小时。在此之后对家长主义法律的理解和运用出现了反复,这突出地表现在就是更为著名的Lochner v. New York案,该案的缘起是纽约州劳动法。该法第十条规定,为了保护面包工人,他们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天,每天不得超过10小时。洛克纳是纽约一面包房主,他起诉该法律侵犯他的“合同自由”和私人财产权,最高法院多数法官判定他胜诉。但当时即遭到最高法院法官之一霍姆斯(Oliver Holmes)的反对,在他著名的“反对意见”(dissenting Opinion)中,霍姆斯说,“美国宪法不应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但“洛克纳案”的判决直到1937年才被翻转过来。
或许有人认为上述案件的判决出于其他的考虑,诸如社会公共利益、伤害原则等等。如果有人认为,对工作时间的要求除了对当事人的身体健康关注之外,还有出于对其家庭其他成员的考虑,因为如果当事人的健康和安全得不到保障的话,依靠其生活的家庭成员以后的生活也无从保障了。即这样的立法的目的是想消除由于对当事人的伤害而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的负担。对此,有学者做出这样的回答:“有一点非常令我奇怪,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热心地坚持认为:那些从伤害中承受的不幸最多的人最不可能从该立法中获益”。但如果我们将这些规定与前已论及的硬家长主义四个充分必要条件相对照,无一不在硬家长主义的范围内。退一步说,也可将其归于混合的直接家长主义范围内。此外,诸如禁止卖身为奴、在婚约中规定不得提出离婚的条款、房屋租赁合同中房屋最低可居住性条款的不可放弃、禁止放弃某些消费合同中“冷静期”等等,无不体现了合同法中的法律家长主义。
行政法家长主义在行政法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健康和社会保障方面。一些行政主体通过对相对人个人行为的规制实现其家长主义的目的。美国经历了一个简短的纯粹家长主义政府规制的阶段。20世纪初,14个州通过法律禁止生产、销售烟草或烟草广告,并禁止在其领域内使用烟草。这种家长主义在1900年达到高峰,最高法院支持田纳西州完全禁止生产和销售烟草,其理由是这些产品有害于健康。但基于纯粹家长主义基础的烟草规制很快消逝了。1927年,反吸烟立法被撤销,甚至法院也不怎么接受纯粹的家长主义规制了。法院认为“除非这种限制能合理地提高公共福利,公民的个人自由不受干涉。”但值得一提的是,至今美国除了四个州之外,其余各州都规定的安全带法,要求驾车人必须系安全带。
1970年代的围绕着苦杏仁苷(Laetrile)的争议是硬家长主义在公共健康规制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苦杏仁是作为一种治疗癌症的药被使用的,尽管在实际上没有研究表明它有临床效果。但是,重症病人努力奋争以获得使用它的权利,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药至少给了他们希望。即便病人们充分认识了其缺点和可能的副作用,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还是拒绝了癌症病人使用苦杏仁的机会。由于FDA不能以伤害原则或软家长主义原则来充分论证其合理性,联邦地方法院和美国上诉法院第十巡回庭认为病人有权利使用。后来最高法院一致否决了下级法院在Rutherford v. 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接受了FDA的观点,因为在药品没有被证明有临床效果的前提下,没有什么利益可以超过服用这种药内在的风险。因为对当事人只有风险没有利益,收益为负,按照选择的经济学模式,他们服药的选择是不理性的,不应支持,所以,FDA和最高法院最终拒绝所有患者服用苦杏仁的权利。
此外家长主义在健康领域还体现在对保健品的规制尤其是对保健品的行政许可方面,保健品法在FDA与保健品生产和销售商之间的斗争达到了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当60年代FDA试图更严格地规制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时候,遭到了消费者的反对并在国会的行为中体现了出来。Proxmire议员认为“真正的问题是FDA是否应扮演上帝的角色”,“如果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安全的,且没有标错标签,消费者就有同样的自由购买,就象他有自由购买其他的食品和饮料一样”。该法最终将维生素和矿物质排除在药品之外。1992年的两部立法,即健康自由法(Health Freedom Act)和保健品法( Dietary Supplement Act),继续了国会倾向于对保健品规制放松的态势。1994的《保健品健康教育法》(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 of 1994 (DSHEA))规定保健品被视为食品,而不是药品或食品添加剂,并将保健品不安全的举证责任交由FDA承担,需要由FDA证明保健品的成分“在推荐的或一般的使用条件下产生一种重大的不合理的危险或伤害”。尽管如此,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部长(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仍有权力宣布“对公共安全和健康迫近的危险”并立即将该产品清除出市场。但这种规制的放松招致了会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即GAO)的批评,会计总署在其2000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关于保健品的松懈的规制几乎没有起到保护消费者的作用。该报告批评了FDA没有建立对结构/功能的详细的证据要求。缺乏证据要求使得该产业缺乏引导以致会导致消费者错误地以为保健品会治疗疾病。虽然关于保健品的规制问题仍存在尖锐的对立,但FDA对于新药发展的规制仍可以被视为力图达到两个目标:禁止未获得许可证的药品进入市场;限制消费者对药品的选择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规制可以被视为家长主义式的,因为此时个人自由从属于政府机关的行政许可的自由裁量范围内。
对药品而言,其结果有点矛盾:在没有规制(规制真空)的时候,选择自由失去了其大多数价值,因为对做出有意义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只有在一些自由退后、有利于规制的时候才存在。一般来说,FDA的规制会实际上提高个人自治利益,其方法是确保支持做出有意义的决定所需要的信息基础。问题是出在两方面,一是规制的细节方面,一是家长主义干预和该机关产生的信息价值的平衡方面。排除其他考虑而只追求个人自由的目的在于提高消费者的福利,但也存在着减少消费者福利的风险。人们只能希望在承认涉及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将新药置于公共市场下的风险的情况下,将来的改革会重新获得一种促使FDA产生新的审查政策的平衡。
在行政法领域里家长主义还表现在社会保障和退休制度上。整体上美国的退休制度经常被比喻成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社会保障是其中的一条腿,雇主负责保障的退休计划是第二条腿,私人的个人储蓄是第三条腿。社会保障系统是最大,最有力的家长主义计划,对雇主和雇工都是如此。而以收入税激励退休储蓄的机制在1974年之前存在,那一年联邦政府通过制定《雇员退休收入安全法案》(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即,ERISA)希望在雇主负责的退休储蓄领域起更大的作用,并创立了退休金利益保证社团。
1974年9月2日,美国总统福特签署了《雇员退休收入安全法案》,如果合乎ERISA的条款,该退休计划就被称为“合格计划(Qualified plans)”,许多公司都愿意遵守ERISA的条款而设立“合格的退休计划”。一旦经过联邦税务局(IRS)或者联邦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的备案和批准,雇主和雇员可以享受包括抵税和延税等最多的税务优惠。如果不合乎ERISA的条款,该退休计划就被称为“不合格计划(Nonqualified plans)”。它没有资格享受所有方面的税务优惠,也就无需联邦税务局(IRS)的核准,故不受IRS的制约。“合格的退休计划”是围绕传统的公司退休金计划、401计划、为雇工利益设置的免税或受教育而追加退休养老金计划以及个人退休帐户计划等等。就雇工而言,如果他们提前从合格退休计划中支取金钱,法律就要求他们交税并加以百分之十的罚款。法典本不禁止在死亡、残疾、退休之前支取该款项,但IRS规定除了五种例外,禁止当事人提前支取并要追加百分之十的罚款。
1997年的《纳税人税务免除法》(Taxpayer Relief Act of 1997)规定了一些相关的个人退休帐户的变化。第一,1974年制订的“传统”的个人退休帐户的法律中规定,该帐户中的钱款如果提前支取用于为家庭成员买房产或接受更要层次的教育,那10%的罚款可以不收。第二,法典中规定了一个新的被称为“ Roth 个人退休帐户”的规则。该规则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所有钱款都是不可扣除的,“合格”的支出则不征税。该规定同原来的个人退休帐户一样,也规定了10%的提前使用罚款。
政府对私人退休金制度的鼓励措施是立足于家长主义的限制。私人退休计划的存在本身就是家长主义式的,法律强制雇员储蓄而不是消费;他们必须现在储蓄以为能在将来收到退休金。
此外,对于特殊群体的家长主义保护也是美国行政法所涵盖的一个领域。这体现在联邦行政机关制定的家长主义政策的发展和应用上。这种行政家长主义的一个例子就是社会保障局的代理收款人计划。1939年国会授权给社会保障局将社会保障利益给受益人的朋友、亲戚或合格的组织。该法还特别强调,不管(regardless)受益人或起配偶是否具有行为能力(competency),都要将该款项交由他人或组织。每年代理收款人计划支付超过20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利益给超过400万美国人的代理人。该计划制定后的50多年中没有受到批评,而且由于使受益人不用管理日常的经济事务,而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但后来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在1988和1989年,几个收款人对该款项的滥用使该政策受到很大负面影响。
国会对与代理支付的基本目标没有明确表述,但是赋予社会保障委员会广泛的执行的广泛的权力。该机关采取了一些基础,在这些基础之上可以发现受益人的利益可以为代理支付所保证。尽管制定法授权给该委员会的主任不管受益人有无法律能力而制定直接支付或代理支付,主任还是发布了规章,要求为绝大多数儿童和州法院认定的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向代理收款人交纳。所有的代理收款人都被要求每年制定一个一页的表格,表格载明是否是为了收益人、的利益而支出,以对委员会负责。收款人乱花受益人的钱,则被要求返还或被提起刑事诉讼。如果该机关认为其在调查或指定收款人的时候有过失,则被要求重新支付被误用的款项给受益人或另行指定的收款人。代理人绝大多数是亲戚朋友,有1/4的是机构或公共官员,只有一小部分是由法庭指定。虽然没有制定法和规章的要求,社会保障委员会的方针提供了为那些州法规定为无能力的人提供的代理支付制度。当没有州法院做出的当事人无能力的判决的时候,社会保障委员会则做出决定,要求代理人为当事人的利益行事。
宪法1、表达自由
家长主义在宪法性法律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商业言论和平等权方面。商业言论(commercial speech)作为表达自由(expression freedom)中的一种,历来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尽管由商业言论的宪法诉讼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但最早引发该诉讼的法律文件似乎应该是制定于1948年的Puerto Rico‘s Games of Chance Act。该法规定为发展Puerto Rico当地的旅游业,允许在当地许可的特定区域开赌场,但任何赌场均不得被允许做广告或其他为当地的公众提供赌博便利的行为,该法律的执行被授权给当地的公共机构行使。后来当地的一个赌场因为做广告被该公共机构罚款,该赌场不服,提起了诉讼。该案最终被最高法院判决维持原处罚决定。Posadas的判决对言论的限制目的在于阻碍消费者从事合法但不受宪法保护的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这个案件被认为是法院曾经经历过的最纯粹的家长主义,法院也支持了这种限制。
自1985年以来,要求限制烟草广告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投票表决提请国会制定禁止烟草广告的议案。在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的一个禁止烟草的广告和促销禁令的合宪性讨论会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授Daniel Hays Lowenstein认为该禁令是合宪的(P1205)。他认为Vincent Blasi教授已经论证了即便在Posadas一案之前,最高法院类似的判决也没有问题。Posadas一案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很显然,如果最高法院如果要否决对烟草广告的禁令的话,需要违反先例。有对商业言论持绝对保护的人认为,在Posasas案件之前的案件都表明对合法产品或服务非欺骗性广告的禁令必然是违反宪法的,Lowenstein教授对此强烈反对。
对最高法院审结的涉及对商业言论进行限制的案件的研究表明:被限制的商业言论越具有便于消费者做出理性选择的“信息”,法院就越有可能否定这种限制。而便于消费者做理性选择这一标准,根据Pope的定义,显然是家长主义式的。在最高法院审结的13个商业言论的案件中,9件被推翻,四件维持。在9件被撤消的案件中,有8件涉及纯粹或主要是纯粹的信息性言论,剩下的一个涉及对促进消耗电力的全面禁止。这样的广告可能是高度具有信息性,也可能是最不具有信息性,或在其中间的某个地方。一般来说,电力的广告很可能比其他消费产品(当然包括烟草)更具有信息性。在4件维持的案件中,没有一件禁令所涉及的主要是信息性的广告。
按照Lowenstein教授的说法,由于家长主义认为国家对待其公民可以象对待孩子一样。这样的观点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所以很少有人承认有家长主义的倾向,更不要说大胆地确认家长主义原则并挥舞家长主义大旗。由此,不难理解最高法院在对商业言论实施拓展的宪法保护的时候,它是以反对家长主义的名义做出。但如果只看法院的行为而不是看其语言,会发现除非商业言论真正服务于家长主义目的,否则一般都会被限制。法院还从来没有否决过一个可能被解释为执行一种真正家长主义政策的对商业言论的限制。如果我们看看法院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很明显商业言论原则不是一个反家长主义的制度。
2、关于宪法平等权
首先,是关于残疾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平等权问题。自《美国残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即 ADA)颁布以来,已经过了持续的检验,最高法院也受理了大量的残疾人权利的案件。.但ADA也在引起大量的争议,这在2002年体现得更为明显。O‘Connor法官认为2002年法院应被记忆成“残疾人法年度”,因为该年度有大量的关于这个“里程碑式”立法的案件。该年有四个案件。其中的Chevron U.S.A. Incorporated v. Echazabal. 具有典型的家长主义特征。
在该案件中,Echazabal患有肝炎,而其所申请的工作岗位由于需要接触的的化学物质对其健康有害而拒绝雇佣他,他因此提起了诉讼。该案件判决认为一个雇主有权拒绝一个残疾的求职者或雇员对某个会给其带来特定危险的工作职位的请求。ADA对残疾规定了三种情况:1,生理或心理上的损害使其行为受到了实质上的限制;2,有生理或心理受伤害的记录;3,该申请人被认为经受了这样的损害。ADA中“资格标准”(qualification standards)包括要求“不得对工作场所的他人的健康和安全有直接的威胁”, 雇主可以此来作为不雇佣该残疾人的理由。ADA对“直接威胁抗辩”做了规定:只有重大的健康和安全危险,而且该危险不能为合理的设施所减轻的时候才能采取相反的措施。该条款还规定了抗辩的程度,将其深化,规定还包括对残疾人自身的健康和安全有重大威胁。该规定还强制性地要求,做出这样的决定必须基于对残疾人能安全地完成工作任务“个人化的评价”,因此应基于依靠当前的医学知识和现有的最好的客观材料做出合理的医疗判断。平等雇佣委员会在其规章中引用了参议院的报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报告和众议院劳动委员会的报告,进而论证了其认为直接威胁包含对自身威胁的观点。
地区法院认为公司有权不雇佣Echazabal,因为如果雇佣的话回对其自身的健康和安全产生“直接威胁”。上诉到第九巡回法院之后,问题直接显现:直接威胁的抗辩是否包括对工人自己健康或安全的威胁?陪审团否定了地区法院的判决,认为:1,对Echazabal自身健康或安全的任何直接威胁不能证明Chevron对ADA规定的确切的抗辩,并因而不雇佣他;2,他的肝所将要承担的任何由于暴露在有毒化学品下而造成的损害的风险并不能阻止他具有ADA规定的“其他资格”。法院多数意见认为,“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并不包括对残疾人自己健康和安全的威胁”。并断定,“通过对只有‘对工作场所其他个人’的威胁的具体化,法律清楚地表明,对其他人的威胁(包括残疾人自己)没有被包括到该抗辩的范围内”。最高法院在指出了第九巡回法庭的判决中的三个逻辑错误之后认为,国会使用类似于直接威胁的条款的决定在复原法里已经包含、而这时国会也知道平等雇佣委员会已经将该文本解释为包括对自己的威胁,这使得那些认为国会将明确地在ADA条款里排除对自己的威胁的观点被排除。因此行政机关的解释扩展了该条款的内容以允许其他的案例发生,亦即包含残疾人对自己的伤害这一情况,所以这并不与ADA的文本矛盾。
虽然该案件由于雇佣劳动关系引起,但其涉及的却是宪法上的平等保护问题,而该案件中地区法院和巡回法院乃至最高法院围绕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EEOC)的规章所展开的讨论证明了这一点。EEOC的规则以家长主义的态度扩张了的ADA对“直接威胁”的定义,认为包括了对自己施加的危险。因此,这个规则用雇主对这个对残疾人雇员或申请者危险的评价的决定,代替了当事人自己的决定,这明显是家长主义的。但是,这个家长主义是存在于美国残疾人立法中80年之久的家长主义哲学的逻辑结果。家长主义态度是长期以来的认为对残疾人的态度的自然延伸,被ADA以默示的方式执行。因此,在对隐藏在ADA默示的家长主义哲学指引下,在Echazabal一案中最高法院一致认为在EEOC规则中明显存在的家长主义上可允许的,因为它要求对申请人或雇员的潜在的危险要进行个人化的评估。这也直接体现在1973年《复原法》(The Rehabilitation Act),因而在语义上和实质上也体现在ADA上的家长主义哲学的自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