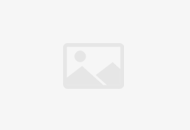她具有反抗精神,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她甚至一度做过农协妇女代表。她敢于把郭举人的“枣子”泡到自己的尿液里,以此来进行报复;她是整个《白鹿原》上最低贱的一个女人,但也是整部《白鹿原》里唯一一个在被男人玩弄的同时也玩弄男人的女人,唯一一个打过男人耳光,唯一一个尿到鹿子霖鹿乡约脸上的女人。但是她这点反抗是不彻底的,她因为自己的反抗而招来了更大的灾难。失去了男人黑娃这个靠山后,她很快向身边的男权世界妥协,寻求其他的男性作为依靠,她也很快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
示例事实上,田小娥原本是一位极其纯朴可爱的传统女性,她强烈地渴望过着正常的生活。在和黑娃的相会中,她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和黑娃厮守终生的美好愿望。文中她三次对黑娃说着同类性质的话:“‘我看咱俩偷空跑了,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小娥呜咽着说:‘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黑娃哥呀,要是不闹农协,咱们像先前那样安安宁宁过日子,吃糠咽菜我都高兴。……’”就是在鹿子霖跟她睡完觉后要给她钱时,小娥还是突然缩回手:“不要不要不要!我成了啥人了嘛?”但是那个男权社会,却不给这个纯朴的女人任何机会。当她跟黑娃的事情败坏以后,她被郭举人扫地出门,赶回娘家;而父亲则气得病倒,只求“要尽快尽早地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用锹铲除在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当黑娃带着田小娥回到白鹿原时,鹿三以断绝父子关系来威胁黑娃放弃田小娥,白嘉轩拒绝他们进祠堂完婚;直到黑娃出走后她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两次被绑到祠堂挨刺刷……直到最后她被鹿三杀死在炕上。田小娥的死是发人深思的。作者让田小娥死于自己的公公鹿三之手,而鹿三是个善良本分的普通劳动者,连他都不能见容,可见男权社会的礼教对田小娥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她的死,是男权社会对胆敢反抗礼教的女性的彻底围剿!
形象文本中田小娥初始的形象是一个反叛宗法文化,追求人性的“叛女”形象。她是作为一个男权社会及其封建伦理纲常的受害者的形象在文中亮相的。她对黑娃的诱惑,虽说有肉欲的放纵色彩,但也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反抗。田小娥人格的转型,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她第一次挨“刺刷”之后。在这之前,她的反抗都是自发的。从第一次挨刺刷之后,她开始对这个男权世界彻底绝望,充满仇恨,并且主动实施报复,此后她开始不要脸皮,她牵着孝文的阳物走进窑洞……但这是一种多么无奈、无力和屈辱的报复,一位柔弱的女子栖身于一方破窑,四面八方是猛如禽兽的男权,她唯一的对抗的武器是女人的身体。这种对抗的结果是她被男权社会彻底摒弃,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荡妇”!
李沁版田小娥
小娥这个形象说明了妇女初期的反抗是出于一种身体的本能,她完全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去反抗传统的封建礼教。周作人认为世界上的妇女解放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女子有了“为人或为女的两重的自觉”。他将“性的解放”作为女性个性觉醒的重要条件,目的无非是使妇女不但明了“自己是一个人”,更能明了“自己还是一个女人”;妇女解放运动只有在此基础上运作,才能“依了女子的本性使她平均发展,不但既和天理,亦顺人情”。小娥就是因为有了一个正常女人的渴望,才不甘屈于那种猪狗不如的生活,才想叛逆。
白鹿原为了和黑娃的偷情。可以说,这是小娥苦难人生的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满足自己欲望的解脱,这种出轨的行为和传统观念完全相悖。
作为一个反抗者,田小娥也曾做过斗争,那就是和黑娃,鹿兆鹏等人在白鹿原上刮起了“风搅雪”,她做了妇女主任。提倡女人剪头发放大脚,禁烟砸烟枪;刀砍奸淫佃户妻女的三官庙老和尚,砸死在南原一带以糟蹋妇女著称的恶霸庞克恭……这一切都是妇女解放的前奏,也是小娥反抗这个社会的表现。
但是,当我们深入的对田小娥的反抗历程做一个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田小娥的反抗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抗,她要利用性这唯一的武器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她比鹿冷氏有更自由,更积极的性爱选择权,她已经认识到女人身体对于男人的意义,并且学会了利用自己的身体去开展“外交”,以获取男人的关注和保护。性爱只是她的手段,改变自己的地位才是她的目的。选择黑娃一方面是本能的生理需求,而另一方面,更重要是为了跳出连只狗都不如的火炕,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屈服于鹿子霖的淫威,是她意识到他对她的作用,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如果她得不到他的庇护,就很难生存,因此在与他的交往中他们获得的满足是双向的,他得到了她的肉体,而她也得到了保护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田小娥这一个女性形象一出现就是背负着原罪的,并一直为此付出着代价。女性的悲惨命运久已有之,自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以后,女性的地位就开始下降,她们没有经济支撑,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惟有依靠男人。“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她们没有能力与男人抗争,除非她们不想生存。也正是这无能为力导致了她们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