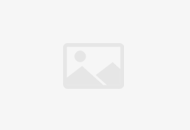求作家三毛的生平简介
姓名:陈平
别名:三毛
生辰:1943年3月26日
祭日:1991年1月4日
籍贯:浙江定海
地区:台湾
国家:中国
职业:作家 剧作家
原名陈平,生于四川重庆。
幼年期的三毛即显现对书本 的爱好,5岁半时就在看《红楼梦》。初中时几乎看遍了市面上的世界名著。初二那年休学,由父母亲自悉心教导,在诗词古文、英文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础。并先后跟随顾福生、 邵幼轩两位画家习画。在沙漠时期的生活,激发她潜藏的写作才华,并受当时担任《联合报》主编平鑫涛先生的鼓励,作品源源不断,并且开始结集出书。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在1976年5月出版。1981年,三毛决定结束流浪异国14年的生活,在国内定居。 同年11月,《联合报》特别赞助她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回来后写成《万水千山走遍》,并作环岛演讲。
之后,三毛任教文化大学文艺组,教小说创作、散文习作两门课程,深受学生喜爱。1990年从事剧本写作,完成她第一部中文剧本,也是她最后一部作品《滚滚红尘》。1991年1月4日清晨去世,享年48岁。
《大道之行也 》的作者及生平简介
选自《礼记》,《礼记》是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到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儒家论说或解释礼制的文章汇编,是儒家经典之一。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说。《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光秦的其它典籍。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
贵州夜郎的来历是什么?
在莽莽苍苍的贵州高原上,二十四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活繁衍,这里是古人类的摇篮之一。春秋至秦汉,这里出现了一个夜郎国,它是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史记》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接二连三的考古发现,渐渐揭开了夜郎的神秘面纱。许多古老的遗存,证实了两千年前夜郎地区确为“耕田有邑聚”。赫章可乐墓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神秘的幽灵世界,这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未知数,隐藏着无数“夜郎之谜”。在这里发现许多不同寻常的青铜器,显示出一种有别于中原的“异质文化”特点。起源很早的铜鼓文化,展示了由铜釜演变为铜鼓的历史脉络。这些奇异的铜器从何而来?普安铜鼓山文化遗址作了明确回答:它们是源于“夜郎人”的创造。
在夜郎的故土上发现的大量陶器,传达出了许多历史信息。作为定居生活的标志,陶器的出现说明人们已在水田农业的基础上定居下来。陶纺轮告诉我们,“衣不蔽体”的原始时代已成为过去;陶器上出现了许多刻划符号,类似中原的“陶文”,当是文字萌芽的雏型。
夜郎的发现极富戏剧性,它是由“枸酱”引出。为了“浮船牂牁江”攻打南越,于是有了“唐蒙通夜郎”。随着汉军的步履,在开发“西南夷”的浪潮中,开辟了“南夷道”,设驿站通牂牁江。最终把夜郎纳入了汉朝的版图,打破了“夜郎自大”的封闭状态。于是,在贵州高原上出现了大量汉墓,中原及邑蜀的文明源源传入贵州。
夜郎--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
中华文化是由“多元”合为“一体”。当汉文化在中原崛起之时,边疆出现了多种民族文化。古文献把云南、贵州及川西谓之“西夷”,云贵谓之“南夷”。在数十个部落之中,夜郎最为显赫,当是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
《史记》说:“平南夷置郡。”史家们据此作出一个基本判断:汉代郡的范围,大体是夜郎的故土,它在巴蜀以南、滇以东,南越之北、武陵郡之西。
回溯贵州史前文化
早在距今二十四万年前,贵州这块土地上就有远古人类栖息、繁衍。在这里发现了属于晚期直立人阶段的“桐梓人”,发现了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水城人”和“大洞人”,发现了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兴义人”、“穿洞人”、“桃花洞人”等等。如果把这些发现也云南的“禄丰古猿”和“元谋人”联系起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幅由猿到人的发展图景,其间并无缺环。因此,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云南高原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考古证实了司马迁所说的“耕田有邑聚”
司马迁把“西南夷”的社会经济分为三种类型,即“耕田有邑聚”、“随畜迁徙”和“或土著或移徙”。夜郎当时的发展水平较高,属“耕田有邑聚”一类,他们已开始耕种水田,定居而成村落。
战国至西汉的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大量的土坑墓群,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陶器和铜锄的发现,有力地证明当时已是“耕田有邑聚”。在汉墓中出土的冥器,虽是汉族移民的随葬品,但也反映出汉时夜郎地区的农业状况。
神秘莫测的古墓
古墓是灵魂安息的地方,它隐藏着许多历史的秘密。现在看来比较偏僻的赫章县可乐乡,古代曾经繁盛一时。这里曾是汉军驻扎的地方,留下许多汉墓,埋葬着外来的汉族移民。这些汉墓总的特点是有封土,考古工作者把它们称为甲类墓。在可乐河南岸分布着另一种无封土的土坑墓,共一百六十八座,称作乙类墓,或称为“南夷墓”。威宁中水乡也有一批类似的土坑墓,有人说它们是“夜郎旁小邑”的墓葬。赫章可乐乙类墓是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时代可上溯至战国。这些古墓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神秘的幽灵世界。
挖开无封土的乙类墓,没有墓道,只见一些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墓坑,坑内有仰身肢葬,也有排葬和乱葬。其中有二十多座墓坑与众不同,坑内无棺木或裹尸的竹席,死者的头部放入一个铜釜或铁釜之中,少数脚下也套有铜、铁釜,考古上把它称为“套头葬”。这种葬式极为罕见,到目前为止,中国其他地区及国外均未见记录。据说广西西林普驮发现了一种“铜鼓葬”,将尸骨全部放在倒置的铜鼓中,另用铜鼓为盖。专家认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葬式,“套头葬”为贵州独有,很可能是“古夜郎人”的坟墓。
不同寻常的青铜器
赫章可乐乙类墓和威宁中水土坑墓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展示出几件稀世之物,不但一般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就连文物鉴定专家也觉得奇怪。例如一字格铜柄铁剑、蛇头茎首铜剑、饕餮纹无胡铜戈、心形铜钺等等。这些兵器不曾见于中原、巴蜀及其他地区,莫不是“天外之物”吧!在云南宣威、曲靖等地也曾发现类似的器物,文化的一致性恰好说明“夜郎人”的独创。
陶器传达的信息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一大发明,它是人们走向定居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在游荡不定的生活中不可能使用易碎的陶器。贵州出土了许多陶器,从新石器时代到西汉皆不乏其物。陶釜、陶壶、陶罐、陶蒸、陶碗等的出现,反映陶器已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之中。铜鼓山遗址中的陶窑,说明当时已可烧制。汉墓中出土的轱轳吊桶陶井和陶碓,是当时人们定居生活的写照。
汉代开发“西南夷”的浪潮
山重水复的夜郎地区,最早与巴蜀并无大道可通,秦代的所谓“五尺道”也只是“略通”而已。
为了联合夜郎攻打南越,唐蒙奏请“发巴蜀卒治道,自道(今四川宜宾)指牂牁江”。其工程浩大艰巨,于是用了数万人,苦心经营了十几年,历尽千辛,开辟了进入夜郎国的道路,史称“南夷道”。据学者考证,“南夷道”从牂牁道开始,经过黔西北而达牂牁江。考古资料渐渐证实,《史记》的记载是有根据的
亦思巴奚战乱的过程
这场战乱分两个阶段:⑴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波斯人、义兵万户赛甫丁与同为波斯人、可能也是义兵万户的阿迷里丁,在泉州发动兵乱。⑵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掌握泉州市舶的那兀纳勾结蒲寿庚(参见《泉州人名录·蒲寿庚》)的后代,在泉州发动第二次兵乱。 战乱的第一阶段是以赛甫丁、阿迷里丁为主导的亦思巴奚军占据泉州、攻占福州以及参与兴化、惠安一带宗族的内战,时间为1357年至1362年间。占领福州1359年(至正十九年)正月,安童和三旦八将原兴化路自立为兴化分省,下辖莆田县、仙游县、兴化县一共三县,由安童任参政、三旦八任平章,扩军备战。二月,赛甫丁也率亦思巴奚军北进福州,经过兴化时与三旦八的部队会合,两军共计数千人共同北上。赛甫丁还留下一支小股部队驻守兴化,与镇守兴化的安童部队协同防守。此时,亦思巴奚军和兴化的安童、三旦八仍是同盟的关系。北上的泉州、兴化联军顺利的攻下福州,扶持普化帖木儿控制了省城福州的大权。而赛甫丁则率这一部的亦思巴奚军长期驻守在福州。阿迷里丁进攻兴化1359年亦思巴奚军北上取福州的同时,留守兴化的那支亦思巴奚军却与安童的兴化部队发生了矛盾,起因是安童麾下的兴化兵对亦思巴奚军表示不服并常常进行挑衅。留在泉州的阿迷里丁得知情况之后,就佯称北上支援福州,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三月率泉州的亦思巴奚军主力北进,在经过兴化路城的时候准备趁机将其占领。安童了解到阿迷里丁的企图,便采纳漳州总管陈君用等人的计策,关闭兴化城门并在城头驻兵、在西门外聚集乌合之众佯作军队,试图以此阻吓亦思巴奚军。当时尚在福州的三旦八连忙赶回兴化,在城外劝阿迷里丁退兵,但反被拘禁。随后,阿迷里丁开始强行攻城,纵火焚烧城门,而安童守军则在城上用水灭火,双方用弓箭互射,僵持了一天不分胜败。第二日,亦思巴奚军从城西发动进攻,先用弓箭手射退靠近山丘较矮的城墙上的守军,再由数百名士兵攀墙而上,一举攻陷了兴化路治莆田城,并纵兵屠杀抢掠莆田县近一个月,其间兴化各地乡族纷纷组织武装以进行防御。莆田城破之时安童成功逃到仙游,但他的妻子和财产都被亦思巴奚军获得。不久,安童又在兴化县龙纪寺重新组织部队进行反攻,而亦思巴奚军也因为莆田当地民众反抗而缺少支持,到了四月,阿迷里丁就带领俘获的三旦八、安童的妻子和强掳来的兴化男性人口回到泉州。还有一种说法称莆田民众不堪亦思巴奚军骚扰而群起反抗,阿迷里丁只得在夜间逃回泉州。亦思巴奚军撤走后,原兴化路同知惠安人柳伯祥进入莆田城安置百姓。兴化内战亦思巴奚军退出兴化后,兴化即陷入内战,各政要和豪强家族相互攻伐。1360年(至正二十年)正月,兴化路推官、莆田县莆禧人林德隆率乡兵从黄石出发,攻占了路城莆田,将时任府判的柳伯祥驱逐,而与柳伯祥同为惠安人且有联姻关系的豪族陈从仁则率其乡兵从另一个方向进入莆田。由于两派势力都很强大,兴化分省长官苫思丁就将二人都授与官职,陈从仁在当年秋季被任命为兴化路同知,而林德隆则在冬季被任命为兴化路总管,二者手中都有军队。林、陈二人矛盾日益加深,到了1361年,陈从仁和他的弟弟陈同(一说为其侄儿)与苫思丁联手对林德隆发动袭击,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其逮捕入狱,并暗中用沙袋压死,对外宣称林德隆是病死的,还将他的尸体焚毁,并派兵把林德隆的财产瓜分。林德隆的长子林珙(也做林琪)逃往福州、求援于赛甫丁,次子林许瑛(也作林瑛)则逃到泉州求援于阿迷里丁,两人都答应帮助林家,于是数次派使者到兴化,要求苫思丁惩办陈从仁。得到亦思巴奚军支持后,1361年(至正二十一年)四月,林珙率其乡族民兵进驻湖头等地,阿迷里丁又派兵进攻惠安一带的陈同部队,二者一南一北形成夹击。苫思丁慑于亦思巴奚军的强大,只好与之密谋,在兴化分省的后堂诱杀陈从仁,并以图谋不轨的罪名肢解了陈从仁的尸体。此时阿迷里丁的部队已经到达仙游县枫亭镇,而林珙部队也进抵黄石,苫思丁就将陈从仁的首级和手臂分别送至两军,二者方才退兵。而驰援来救陈从仁的陈同在莆田城南门外听闻陈从仁的死讯后,便逃往漳州投奔漳州总管罗良。亦思巴奚军随后护送林珙到兴化继任其父的兴化路总管职务。不久后苫思丁调回福州,元朝政府派遣参政忽都沙、元帅忽先管理兴化分省。陈同在漳州得到罗良的支援,后又潜回惠安联系姑父柳伯顺(柳伯祥之弟)。1361年六月,陈同带领漳州援兵乘船由海路抵达家乡惠安,并攻下惠安县城,在杀死县吏后,强迫惠安县民众入伍,并和柳伯顺的民兵部队联手出兵兴化,为陈从仁复仇。陈、柳联军不久就在仙游枫亭击败了刘希良、林子敬、陈县尉等人率领的林珙军,并由柳伯顺及其麾下的杨九、黄国辅一路追击到莆田吴山、下林等地,沿路多有烧杀行为发生。为了顺利攻下莆田城,陈、柳方面利用了兴化路掌握军权的忽先和掌管政务的忽都沙之间的矛盾,暗通忽先,在七月时里应外合攻陷莆田城,由杜武惠、胡庆甫、林全、李德正等部将带兵由莆田西门进城,胁迫忽都沙交出政权、并下令莆田军民讨伐林珙。随后,林许瑛再度逃往泉州求援,阿迷里丁派扶信率领亦思巴奚军于八月猛攻莆田,驱走了柳伯顺。九月,亦思巴奚军进城并迎林珙回城,扶信自称元帅,林珙自称总管(也有说以林瑛为总管的)。而柳伯顺则逃往兴化县、忽先逃回福州。另一路亦思巴奚军在麻哈谋带领下攻占仙游,胡兴祖、上官惟大则进兵兴化县进攻柳伯顺,至此,战火烧至兴化路全境。 战乱的第二阶段是那兀纳通过兵变取代阿迷里丁而占领泉州,并割据泉州直至被陈友定的军队消灭。那兀纳兵变扶信率亦思巴奚军主力北上进攻兴化之后,泉州城防守变得空虚,到了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二月,原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的孙婿、逊尼派穆斯林那兀纳趁机发动兵变,袭击并杀死了阿迷里丁,并在泉州大肆搜捕阿迷里丁的亲信党羽,将亦思巴奚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了泉州的统治者。而当时带兵在兴化的扶信只得到福州投靠赛甫丁,而赛甫丁仍然扶持林珙为兴化总管。到了1362年4月,元朝委任燕只不花接替调往江浙的普化帖木儿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但驻守福州的赛甫丁却紧闭城门、拒绝让燕只不花进入。燕只不花于是调集包括陈友定的部队在内的福建各路兵马合攻福州,林珙的兴化军队也在征召之列,但林珙借故推脱,燕只不花就调江西行省左丞余阿里到兴化负责防御事宜。屡败赛甫丁,并将福州城围困长达三个月,赛甫丁最终接受调停,率军登船从海路离开福州回到泉州,而福建行省参政观音奴还在赛甫丁和扶信上船之后袭击尚未登船的亦思巴奚军士兵数百名,赛甫丁从此失势。那兀纳对泉州的统治那兀纳在泉州用残忍的方法统治和搜刮人民,甚至用强夺的方式敛财,并将许多抗拒的民众杀死,借此得以聚敛大量财富,他把泉州所有的非蒙古人的官员全部驱逐,还从民间遴选了大批女子作为他的妻妾,以观看这些女子捡取他撒于楼下的金豆为乐。他还兴建了极为华丽的清真寺,将搜到的财物积存于寺中,生活骄奢淫逸。政治上,那兀纳一开始与福州的燕只不花有着一定的默契,以此对抗其他势力,甚至抵触元朝中央政府。1364年至1365年,元朝政府设置兴化分省、兴泉分省和泉州分省的计划都被那兀纳和燕只不花破坏,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十月,那兀纳甚至直接和奉元朝皇太子之命从大都来福建设置兴化、泉州分省的福建行省左丞观孙发生冲突,阳奉阴违,拒绝服从元朝中央政府的命令,最后逼迫观孙离职。兴化内战渐息在兴化的问题上,那兀纳延续了阿迷里丁对抗陈同、柳伯顺家族武装的政策。泉州那兀纳兵变发生之后,柳伯顺和陈同又于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三月伺机发动反攻,分别攻克兴化县和仙游县,柳伯顺又强迫兴化县民众入伍,准备和陈同夹攻莆田城,但陈同爽约,柳伯顺部队只得单独进攻莆田城宁真门,守城的林珙方面军心畏惧、陷入困境。这时恰逢亦思巴奚军的两个骑兵从泉州抵达莆田,林珙就利用这两位番军骑兵打头阵,率领莆田军队出城迎战,谎称是泉州亦思巴奚大军来援。柳伯顺的部队信以为真,准备不足,因而大败而归,士兵阵亡上千人。当年六月,柳伯顺再次驱遣兴化县民兵进攻莆田县,但再次惨败,损兵上千。由于两次进攻莆田的企图都告破灭,柳伯顺便领兵盘踞在兴化县,不轻易出击燕只不花占领福州后,委任余阿里到莆田城管理兴化分省,不久,又由参政郑旻接替余阿里。郑旻着手调解林、陈两家的世仇,终于让林珙离开莆田城,返回其家乡莆田县莆禧,并让陈同、柳伯顺停止军事行动。虽然停火,但兴化路依然形成了四分的局面,柳伯顺割据兴化县、陈同盘踞在仙游县、林珙和林许瑛则拥有莆田县的新安里、合浦里等十几个里,而郑旻所管辖的兴化分省实际上只控制着莆田城及附近几个里的很小的范围。虽然林、陈两家族停火,但在仙游县却又有新的家族武装冲突发生。1362年五月,在陈同和柳伯顺发动对林珙的反攻之后,又率领一千多士兵进攻仙游谢岩的豪族谢必恭家族,以报复当初谢氏家族拒绝兵败的陈、柳二人借兵借粮的请求。陈、柳军队顺利攻下谢岩,并劫掠了谢家的人口、财产,焚毁其房屋。为了报仇,谢必恭于1362年十一月从尤溪县招募一百多名亡命之徒进攻陈同辖下的仙游县,但在龙华寺被镇抚詹伯颜所击败。一年之后的1363年十二月,谢必恭又联合土官郑深甫、钱鉴等率领两百多名尤溪民兵从九座山间道进攻仙游县,柳伯顺亲自率领部队在廉洁里击败谢氏军队,并追击到柘山、俘获了谢必恭,最后在龙华寺将谢必恭毒死那兀纳进攻兴化1363年十一月,那兀纳派遣部将博拜(又作白牌)、大阔先攻陷陈同据守的惠安县,然后又攻陷了仙游县以搜捕陈同,并将军队驻扎于枫亭,之后继续向兴化县的柳伯顺进攻,兵临龙纪寺,在搜索柳伯顺无果之后返回,驻扎在枫亭。1364年正月,那兀纳指责兴化分省长官郑旻串通陈同、柳伯顺,因而引兵进逼兴化路城莆田,在撤换官员、杀死柳伯顺所派的官吏之后,才在福建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德安的要求下于二月撤军。1365年三月,福建行省左丞贴木儿不花被委任主持兴化行省,前摄分省事郎中德安作为他的参赞,这一安排再次引发那兀纳的不满,他以追取军储为借口派泉州官员和其麾下的湖州左副奕军三百人进入莆田城,横行内外,最后逼帖木儿不花回到福州,而德安则以郎中之职留在兴化,这时那兀纳方才撤军。十一月,元朝皇太子再度派前左丞观孙前往兴化、泉州负责分省事宜,但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为阻止元朝中央政府的插手,暗地里命令兴化的德安想方设法拒开观孙。于是德安召集了大量民兵,连同福建行省派来的孟孙两同佥兵合力据守兴化。为了增强实力,德安又向泉州那兀纳求兵,于是那兀纳就派通事哈散、惠安县尹黄希善带领正规军和民兵部队进抵莆田城下,这时哈散又想赶走两同佥兵,于是双方爆发冲突,同佥兵击溃了泉州部队。因为害怕亦思巴奚军的报复,莆田全城百姓连夜逃走,连德安也在次日离开。不久,哈散、黄希善、马合谋、白牌就带领亦思巴奚大军入城,又还纵兵抢劫涵江、江口、新岭,甚至把战火烧到了福清的蒜岭、渔溪、宏路一带,所到之处烧掠一空,这些行为引发了兴化人对亦思巴奚军的强烈仇恨。同时,陈同和柳伯顺开始转向福建行省政府寻求支持,行省派兵进驻常思岭,并派左丞郑旻、郎中易里雅思劝白牌等将军退兵,但白牌等拒绝服从行省命令,直到那兀纳下令撤军,才率部返回泉州。1366年正月,白牌、金阿里等又率领亦思巴奚军攻陷兴化县、仙游县进行杀掠。此时,连林珙也开始与陈同、柳伯顺和解,决定共同对抗那兀纳,1366年二月,林珙、柳伯顺联兵,派李佛保、许应元突袭并攻占了亦思巴奚军哈散、黄希善占据的莆田城,杀死数十名番兵、俘获哈散并押往林珙所在的莆禧处决,又派杜武惠胁迫一千名民工修筑涵头寨。仙游的白牌、马合谋在听说路城失守后就撤回泉州。那兀纳随后出兵反击,于三月由枫亭经沿海一线北上,亦思巴奚军在博拜、麻哈谋、金阿里等率领下再度占领兴化、仙游两县,并在吴山向林珙发动进攻。林珙据守蛎前寨,而林许瑛则由海路增援,但白牌、马合谋、金阿里在海上大败林许瑛部队,并进兵攻陷莆禧,缴获了林许瑛的妻子和财产,并将林氏的祖坟、房产、营寨全部毁掉,还在笏石以南两半岛的新安、武盛、奉国、醴泉、合浦一带烧杀抢掠。孤立无援的林珙只得撤退。 亦思巴奚军发动内乱、对抗福建行省的行为迫使行省官员决定完全消灭那兀纳势力。1366年三月,白牌、马合谋、金阿里转攻柳伯顺镇守的莆田城,进兵熙宁桥,包围了莆田东南西北四门,只有宁真门没有遭到进攻,莆田形势危急。早先曾在闽西与红巾军作战的陈友定的精锐部队接到福建行省的命令,被调往兴化增援柳伯顺部。陈友定派遣其子陈宗海率军于1366年四月连夜从宁真门潜入莆田城,并在次日从西门、南门出城对围城的亦思巴奚军发动进攻,这批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迅速击溃了亦思巴奚军,在这场战斗中,亦思巴奚军有数千名士兵阵亡,白牌、马合谋、金阿里也被俘杀,剩余的士兵疲于奔命,却在沿途不断受到对其恨之入骨的兴化农民的袭击,最终仅有4名骑兵回到泉州。莆田之战获胜后,陈宗海立即着手组织对泉州的总攻。五月,陈宗海调发元朝水陆两路军队,水路部队由林珙带领,而陆军在柳伯顺部队配合下由北面向那兀纳的大本营泉州发动进攻,而那兀纳则强征民众入伍,以抵抗元朝军队。陈宗海军的监军陈铉原是泉州洵美场司丞,他暗中联络晋江县尉龚名安、千户金吉等人做接应。金吉也是色目人,属于什叶派穆斯林,因而对逊尼派的那兀纳有不满。在泉州之战开始后由龚名安率水军进入东山渡,并引导陈宗海的水军进攻泉州城,而金吉则在城内打开城门迎接。在里应外合之下,那兀纳最终兵败被擒,并被押往大都(也有说押往福州的)。亦思巴奚兵乱以元朝政府军成功镇压亦思巴奚军,平息兴化、泉州一带的战乱并重新控制泉州而结束。
亦思巴奚战乱的后果
持续10年的“亦思巴奚战乱”,严重地破坏了福、兴、泉沿海一带的社会秩序、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泉州地区受害尤为严重。 泉州是兵乱的爆发点,“郡城之外,莽为战区”(《岛夷志略·吴鉴序》),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造成民众贫困饥谨,出现前所未有的“食人”悲剧。当时泉州开元寺高僧大圭《梦观集·吾郡》(参见《泉州人名录·大圭》、《泉南著述·梦观集》)生动真实地描述:“吾郡从来称佛国,未闻有此食人风。凶年竞遣心术变,末俗何由古昔同?市近袛今真有虎,物灵犹自避生虫。诸公食肉无充半,急为饥民散腐红!” 泉州广大人民备受蒲寿庚家族的压榨和“亦思巴奚战乱”的蹂躏,亦思巴奚军在兵乱期间对福建沿海莆仙、泉州两郡的汉族百姓多有杀戮,对泉州、兴化一带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的破坏,百姓饱受战乱,死伤无数,尤其在那兀纳统治泉州期间大肆搜刮财产和奸淫汉人民女,屠戮泉州汉人,对泉州社会造成重创 。在平叛战争中和乱定之后,激起民族复仇情绪,致使许多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的商人、不法传教士和暴徒,遭到报应。《清源金氏族谱·丽史》称:“是役也,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悉令具五刑而诛之,弃其哉于猪槽中。”《清源金氏族谱·丽史》又载,洪武七年,明·太祖鉴于“亦思巴奚”祸乱,在大赦天下的诏旨中特别规定:“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锢,世世无得登仕籍”。 张星烺认为,亦思巴奚“乃蕃号也,非名。”(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1936年)关于亦思巴奚军名字里“亦思巴奚”的意义,史学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亦思巴奚来源于波斯语的“سپاه”(sepâh),即民兵、骑兵的意思,或是其派生词,也可能是波斯语“义兵”之意,有别于正规部队。朱维干《元末蹂躏兴、泉的亦思法杭兵乱》(泉州文史,第一期,1979年)、庄为玑《元末外族叛乱与泉州港的衰落》(泉州文史,第四期,1980年)认为,亦思巴奚是波斯名城亦思法罕,即今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南的波斯古城“伊斯法罕”城。 1953年,日本学者前岛信次认为:“亦思巴奚”,同由波斯文“亦思丁”(意即“军队”)派生出来的一个词,很可能是“亦思巴奚泉州”(ISpah-i-ehuanchou),与意“士兵”或“骑兵”的单词“思巴奚”(Sipahi)有关联。(日本·前岛信次《元末泉州的回教徒》,东洋文库英文纪要·第32卷,1974年版)努尔《亦思巴奚》一文据波斯语词典提出,亦思巴奚为波斯语“亦思巴呵”、“巴思呵”,意为民兵、骑兵。(《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 吴幼雄《论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认为:“所谓‘义兵’,是为保卫元朝政府,根据临时需要而组建的地方武装”,是“乡兵、民兵之类”。“‘义兵’之含义与波斯语‘亦思巴奚’的意义相近。则知所谓‘亦思巴奚’为波斯语的音译,而所谓的‘亦思巴奚战乱’,即由波斯人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等人为首的‘义兵’加入其中之战乱。”(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政府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陈达生亦同意“义兵”说。他援引前岛信次的考证,指出“亦思巴奚”的外文音译,是指以侨居泉州的穆斯林为主力军队的称号。又考证“亦思巴奚”是阿拉伯语的波斯外来语,其意有三,即:民兵、义兵、骑士、特种部队骑士、特种部队骑兵之意。而“义兵”是元廷根据需要临时组建的民兵、乡兵,有别于正规部队。(陈达生《“亦思巴奚”名称小考》,泉州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1982年油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