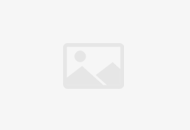爱情与文学什么关系?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旋律,爱情则是文学不变的主题。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迁,爱情和文学,都会保持着一种不变的联系穿梭于时空之间。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永远是最动人的乐章,女人是爱情中最让人思绪飘逸的芳香,男人是爱情中酿造醇香的酒坛,男人与女人的故事不知道产生了多少千古绝唱和秀美鸿篇。千百年来这沁人心脾的美酒一直同文学纠缠在一起。
爱情和文学是要用心去经营的。没有用心的爱情就象风雨中飘摇的茅舍,经不住洗礼,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大难临头各自飞”;文学也需要经营,它需要不断的斟酌、推敲;需要“采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的提炼和浓缩;需要对生活特有的感悟和敏锐的意识。有关爱情的文学作品必然要经过一番内心的良苦思量,而文学中的爱情一定是用心经营后的修来正果。有这样一个故事:普赛克是一位伟大国王膝下三女儿中的小妹妹.她外表和心灵美丽无双,人们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地来敬仰她的美丽.这一切使得美神维纳斯心生妒忌,因为世人忽视了她的美丽甚至忘记了她的存在.于是维纳斯心生一计,她让儿子爱神丘比特设法把普赛克嫁给世界上最丑恶凶残的野兽.丘比特的爱情之箭可以让任何人跟他为他们选择的对象堕入情网,计策本来是万无一失的.但维纳斯忽视了一个细节,一个爱情故事中最致命的细节.当丘比特见到普赛克时,他自己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她.他不仅没有把普赛克嫁给毒蛇,反而把她秘密带到了自己居住的辉煌宫殿,并娶了她为妻,只是不允许她看见自己的容貌。但是此举遭到了维纳斯的阻拦和破坏。因此维纳斯交给普赛克一件又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从凶狠的绵羊身上剪取金色的羊毛,从死亡之河中汲取黑水.每一次维纳斯都自信普赛克根本无法完成,但普赛克每次都得到意想不到的帮助,完成了任务.经过重重的磨难,丘比特和普赛克终于正式成婚.甚至维纳斯也很高兴.一来他儿子有了一个般配的妻子,更重要的是普赛克居住在天堂而不再生活于人间,世界上的人们便不会再为普赛克的美丽所吸引,而会继续崇拜美神维纳斯。
这个神话故事就是文学与爱情的相互融合:把用心的爱情用心的融入文学作品中,使文学充满着爱的温馨,呈现着美的情感,将爱情通过符号化的过程跃然纸上,让文学中的爱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爱情的萌芽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又是以一定的感觉为前提的。什么是爱情的前提感觉呢?那有可能是一见钟情,就像宝黛的木石之恋,虽然二人没有婚姻之缘。“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好生奇怪,倒象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第一次相见的感觉就是他们钟情的见证。现实中因为一见钟情而发展到二见倾情,到最后的互献真情,也是彼彼皆是。爱情是每个人都怀揣着的一种感觉,但是你一直都感受不到。直到某一天,你遇见一个人,那人就好像一直在地球上的这个角落等着你, 在你生命的这一刻终于等到你,好像是你的传说一样。然后,你会突然从他的身上,发现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一种美丽得无法抗拒的感觉。那还可能是一种牵肠挂肚,一种相知相惜,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痛。再说文学作品,它的产生也是受一定的感觉所支配的。这种感觉是作家心灵的蓦然领悟。那是独特的艺术发现,是作家独特的眼光和非凡观察力的凝合。可能是作家不经意的“浏览”,而这个事物的外在机缘又恰好和作家个人的情感体验相契合,这时就产生了对艺术和情感的独特发现。在艺术发现的影响下,产生了创作动机,于是在作家心理失衡的情况下,在外在事物的触动下,形成易感点,这应该就是作家创作之初的感觉。
可见,爱情和文学都是需要感觉的。没有这个特殊的感觉,就不会产生刻骨铭心的爱情,也不会产生许多因为爱情的融入而诞生的优秀文学作品。爱情和文学的感觉,在本质上就是相通的:爱情是文学的核心,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是爱情的心灵驿站,是爱情的艺术呈现。多少文人骚客追求爱情的幸福、体验爱情的滋味、书写爱情的心灵,爱情枯竭的灵魂意味着文学的终结,多少人无法走出爱情的围城,却不小心走进了文学的天堂。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多少人相信万事万物的联系还有无功力性的存在?又是在爱情和文学中,我们可以找到人类最纯洁、真挚的情感。关于爱情的无功利性,虽然不能否认鲁迅的“爱必有所附丽”,但当爱情同整个社会状态进行比较的时候,它还是纯洁的。也许你已经不再相信世间还有真情在,可是我们的身边还是会时不时的充沛着爱情的感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千古绝唱,当爱情降临时,即使会面对生与死的抉择,有人还是会义无反顾的选择后者。如果说为了所爱的人可以把最宝贵的生命都放弃,那还有什么事情会作为功利因素阻挡在真正相爱的人们之间呢?爱情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在文学作品中,它一直是人们追求的一个永恒的主题。那些真正能震撼古今、流芳千古的爱情故事也是无功利爱情的真正体现。不论文学作品,还是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演绎着的多少爱情故事大都以悲剧告终,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也许只有悲剧才有震撼人心的伟大魔力,才能推动人们一步步地走向真正爱情的门槛:梁山伯与祝英台,焦仲卿与刘兰芝,都为我们展示了《汉乐府》中那“山无陵,江水为竭,东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款款深情,也正是这涤荡了功利的真情,为后人上了一堂堂爱情教育课。而文学也深深的打下了无功利的烙印,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是指作家或读者的创作或欣赏活动不指向直接的实际利益满足的特性。文学的这种无功利性集中体现在作家的创作活动和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要舍弃直接的功利考虑而以淡泊之心对待,同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需要保持无功利目的才能进入文学的审美世界。正因为作家和读者的这种平和心态,让文学变成了一方净土。在古代,作家的创作强调艺术的独一无二,也没有同读者直接构成利益关系,虽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变得日益复杂,但是文学的无功利行还是会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的。
“爱情原如树叶一样,在人忽视里绿了,在忍耐里露出蓓蕾”,爱情和文学一样,唯有始终如一、坚持到底的精神和毅力才能酿造出芳香的美酒;“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爱情和文学一样,都是凭着一种最独特的感觉开始它的美丽旅行;并不是要达到了怎样的目的,爱才成为爱,文学才成为文学。从落后的过去到繁华的今天,爱情和文学怀着不变的情怀,携着手,穿过时空的隧道,向我们证明着唯有在它们的世界里才能证明出的美丽。
古代多子家庭起名排序
“叔,少也。”——这个字也跟“俶”字同根。《尔雅"释诂》“俶,始也”,“俶,作也”,就是才起来的,新生的。
“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这个字《说文》认为上面的禾是“稚省”,比于幼禾,总之是最幼少的。不管多于或少于四个,“季”都是最末的,如果只有三个,它就是老三。“春夏秋冬”就因各都分“孟、仲、季”三个月(如孟春、仲春、季春),因而称为“四季”。文王之父季历是老三,上有“太伯、仲雍”,所以末子为老三也可称季。晋代著名道家葛洪字稚川,他也是老三,“稚”即是季的代换字。
从史实看,除以“季”为末子外,伯仲以外叫“叔”的为多。周武王分封诸弟皆称叔某,因为他是老二。请看《史记"管蔡世家》: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 以上老三至老八皆为叔某,老十即老小才叫“季载”。老四周公旦用了尊称,但下文就说“封叔旦於鲁而相周为周公”。屈原《天问》也说“到击纣躬,叔旦不嘉”,都用“叔旦”。因为他只是老四而不是老小,所以并不叫“季旦”。古代名字是分时段取的,先取小名,名,最后才取字。如曹操小名阿瞒,名操,字孟德。字以表德,名与字的字义要相应,如操德皆指品行,孔子的儿子名鲤字伯鱼。取字是冠礼时(正常是在二十岁)之事,其时兄弟排行当可排定了。 此外,纬书所记传说中还有“皇氏五龙”的“伯、仲、叔、季、少”的叫法。《春秋命历序》:“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驾龙,号曰五龙”。只有五兄弟的,也可依此排行,把最幼少的叫“少”,像前面金庸先生的那个例子,叫“史少捷”就比“史孟捷”要妥帖些。
现代取名用“伯仲叔季”就不方便了,因为取名早,不知道哪个才是老小。我当年在浙江乐清调查方言,发音人是有学问的赵一老先生。赵一先生有十一个孩子,他开初就先依“伯仲叔季”取名为“伯子、仲子、叔子、季子”(只论排行,不分男女,叔子就是一位清雅的姑娘,当时也帮着父亲辅助发音)。下面的孩子他并不循环,而称“春子、夏子、秋子、冬子”,老九直叫“玖子”,生了老十,先生想该是末尾了,就取了末子这样意义的字,不想后来又生了最小的十一子,乃取名为“土子”,土者,十一之合文也。如果在古代,应该是这位“土子”兄弟才能叫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