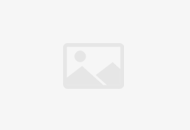花部
搬演历史故事,是花部戏的主要内容。19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暮色黄昏。在中国人灵魂深处普遍蕴藏着的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反叛心理,强烈地体现当时的戏剧中。水浒戏是元明时期就有了的,地方戏艺人本着一股对已处末世的封建统治的挑战精神,将一个个逝去的草泽英雄重新举到了台上。演的虽是宋朝旧事,却紧紧切合着清末时代的脉搏。《打渔杀家》借一个年迈的水浒英雄,在压抑、忍让之中不得不走向反抗的悲壮而苍凉的故事,浓烈地传摹了社会政治意向和时代气氛。父女在江边诀别的绵绵情意,震撼了无数观众的心。除了明显带有反抗色彩的水浒剧目以外,地方戏中还有大量的三国戏,隋唐戏,杨家将戏,呼家将戏。在三国戏里有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有超凡绝伦的军事谋略;在杨家将戏里有忠勇与奸佞的比照,有孤单孀妇与驰骋沙场的呼应……。尽管这些戏也多关及朝廷,但它们大半是从民间心理逻辑出发,表达着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揣想。
清地方戏还把戏剧的独角伸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之中,展示他们的平淡和不平淡的喜怒误用乐。《张古董借妻》是一个民间生活小戏:不务正业的张古董利欲熏心,竟想出了把老婆借给结拜兄弟以骗取钱财的主意。谁料这对假夫妻被强留在岳父家中过夜,而张古董却如热锅上的蚂蚁,被困于城门。他去告状,碰上了一个糊涂官,结果把妻子判给了结拜兄弟。
《百花亭》剧照
花部演出的喜剧和武戏是非常引人注意的。社会民众在生活中充满着艰辛劳苦,但在舞台上却创造着欢乐和热闹。劳作之“苦”与艺术之“乐”使他们获得心理平衡和情绪宣泄。在这些民间小戏里,没有沉重无比的冲突和严肃异常的人物,时时呈现出一种活泼之态和游戏精神。至于武戏,则在历史故事剧中得到突飞猛进般地发展。刀枪剑戟,十八般开艺,在舞台上尽情施展。自然,这成为花部戏对中国舞台表演艺术的重要贡献。相对于雅部」而言。又称「乱弹」。此据《扬州画舫录》卷五引文,显以「乱弹」统摄花部诸调可知(参见【雅部】条)。徐扶明〈乱谈乱弹〉一文研究指出,「乱弹」又名「鸾弹」、「烂弹」、「乱谈」,本来就是「乱弹琴」的意思。其系指花部腔调剧种之音乐风格较活泼嘈杂,取其花杂之义,不类清音。所以,在清代不论梆子腔、西秦腔、吹腔、二簧调、弋阳腔或时调小曲等,都有以「乱弹」一词作为代称或自称的例子。而据乾隆朝江、浙剧坛之地方戏代表总集《缀白裘》的记载,其标目「梆子腔」者,收录了昆腔以外的各式腔调剧种。故花部乱弹,彼时似又可名为「梆子腔」。但这是因为南北戏曲声腔交流所产生的过渡现象。此「梆子腔」并非「秦腔」,而是秦腔或西秦腔与昆弋腔交化后所衍生出来的新复合声腔,由安庆、扬州班子演出,下启江、浙乱弹之二凡和三五七。
高腔高腔是由弋阳腔衍变而来的。由于弋阳腔一开始就具有“错用乡语”、“只沿土俗”的优点,因此它不为一地的方言土语所囿,盛行各地,并在流传过程中,与各地的土声土调相结合,产生了一些各具地方特色的新的声腔。而这些新产生的声腔
又都保持羊着弋阳腔“一人唱众人和之”的帮唱特点其腔高调喧,故在清代,统称这些由弋阳腔衍变而来的戏曲声腔为高腔。
梆子腔《贵妃醉酒》剧照
梆子腔又称秦腔,最早形成于山陕一带,它是在民间小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已经出现了山陕梆子腔的曲调,如明万历抄本《钵中莲》传奇中就已采用了「西秦腔二犯」这一曲调。李调元《雨村剧话》也有记载:“今以山陕所唱小曲曰西曲,与古绝殊,然亦因其方俗言之”另外在《缀白裘》中有一出《出塞》的戏,其中也用了“西调”这种曲调可以说,这种“西调”即梆子腔的雏形。到了康熙年间,梆子腔就已经初具规模,成为一种新兴的戏曲声腔。它一方面盛行于山陕地区,如清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记载,乾隆年间在陕西的西安汇集了许多梆子腔戏班。另一方面,梆子腔已经向外地流传,据《秦声撷英小谱》、《扬州画舫录》等书记载,乾隆年间,梆子腔已流传到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江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四川、云南、贵州等十多个省份。而且,山陕梆子腔流传到各地后,也逐渐与当地的土声土调相结合,演变成为具有当地特色的梆子腔。如《秦云撷英小谱》说:秦腔流传到燕、京及齐、晋、中州,音虽递改,不过即本土所近者少变之”。故也形成一个风格多样的梆子腔唱腔系统如山西有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陕西有同州梆子、中路秦腔、西路秦腔、南路秦腔,河南有豫东调、豫西调、南阳梆子,河北有直隶梆子、卫梆子、老梆子、蔚州梆子,山东有高调梆子、莱芜梆子等。皮黄腔花部乱弹
皮黄腔是由西皮腔和二黄腔结合后形成的一种戏曲声腔。西皮腔是陕西的梆子腔流传到湖北襄阳一带后,与当地的土声土调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声腔,故又称襄阳调。所谓“西皮”意思是指来自陕西的曲调。因湖北一些戏班称曲调为“皮”二黄腔最早形成于安徽,如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载:安庆有以二黄调来者”。在道光年间,以唱西皮为主的湖北戏班与以唱二黄为主的徽班同时进入北京,同台演出,等到西皮和二黄这两种唱腔融合后,便形成一种新的声腔,即皮黄腔。柳子腔柳子腔,起源于山东,它是集合当地流行的民间小调作为唱腔的,所谓柳子,即小调或小曲之意。早在康熙年间,《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就用家乡小调来编撰戏曲,如《襄妒咒》一剧,就用了「西江月」、「山坡羊」、「皂罗袍」、「耍孩儿」、「黄莺儿」、「香柳娘」、「银纽丝」、「呀呀油」、「罗江怨」......等小曲。这些民间小曲有些虽与南北曲的曲调名相同,但唱法则异,用法也不同,没有传奇那种联曲体的严格曲律。如《禳妒咒》剧中所用的曲调,多不成套数,有的一出戏就只用两三种小调,而每一种小调又连用四五支到七八支,在演唱时为了避免重、呆板,故也分紧板、慢板,调整节奏。
花部诸腔戏的兴起,与其本身所具有的群众性、通俗性有关。从剧目上来看,花部诸腔戏多是演出一些为下层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剧目,或为历史故事,或为民间传说,如有关“三国志”、“水浒传”、“杨家将”、“列国志”【东周(春秋战国)故事】、“明英烈”、“东西汉”(两汉)、“说岳”、“隋唐”等讲史演义或传奇故事的剧目。而且通过这些剧目也曲折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故为劳动人民所欢迎。再从艺术形式上来看,花部诸腔戏的唱腔明快激烈,字多腔少,而且曲白皆通俗易懂,符合下层劳动人民的欣赏水平和艺术情趣。因此,劳动人民把这些土生土长的地方戏曲看成是自己最好的娱乐形式。焦循《花部农谭·序》中曾说: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这就表明花部诸戏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也是花部诸戏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花部诸戏的兴起,取代了昆山腔在曲坛上霸主地位,使我国的戏曲艺术自宋元南戏产生以来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革,即由原来的联曲体变成了板腔体,从此结束了戏曲史上的传奇时代,开始了新的乱弹时期,从而使我国的戏曲艺术更加丰富多彩。
新兴剧种乾隆年间(1736-1795)除昆腔以外的地方戏被称为“花部”或“乱弹”,包含梆子、皮簧、弦索等新兴剧种。“花、雅”之分,沿袭了中国历代统治者分乐舞为雅、俗两部的旧例。所谓雅,就是正的意思,当时奉昆曲为正声;所谓花,就是杂的意思,指地方戏的声腔花杂不纯,多为野调俗曲。
如果说,明清传奇是以文人剧作的繁茂为标识的话,那么花部乱弹则恰恰相反,它极少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扶植和帮助。作品直接取自民间,荡漾着泥土的芳香与生命的激情。花部创作可视为是对昆曲雅化倾向的逆反运动。它文辞欠讲究,甚至文理不通,缺少文学上的规范与格式。花部乱弹是在舞台演出与戏剧性上,张扬自己的优势。不论组织戏剧冲突,还是塑造舞台形象,它丝毫不比前代的杂剧、传奇逊色。可以说,花部的艺术性是在舞台上锤炼出来的,而不是案头上推敲出来的。由于剧作家的匮乏,清代地方戏创作始终未能出现像关汉卿、汤显祖那样的大师。中国戏曲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以剧本文学为中心向以舞台艺术为中心的转移。清地方戏作品主要靠梨园抄本流传或艺人口传心授,刊刻付印的极少。保存至今能看到早期面貌的剧本,只有乾隆年间刊刻的戏曲选本《缀白裘》。
在艺术形式上,花部戏当中的梆子、皮簧等剧种,为了达到通俗易懂,从根本上脱离了曲牌联套的结构。它们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的排偶唱词,代替传统的长短句。唱腔音乐则是以一对上下乐句为基础,突出节奏、节拍的作用;以唱腔板式(如慢板、愉板、流水板、散板等)的变化,表现戏剧情绪的变化。板腔体的出现,是中国戏曲结构形式的变化。它可以根据作品的内容,需要唱就唱,不需要唱就不唱。从此,一个戏不必都以唱为主了。不同的作品(或作品内的不同场次),也可以分别处理成唱功戏、做功戏、武打戏等。显然,这有利于中国戏曲唱念做打的综合性、整体性向更自由灵活的形态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的戏曲剧种,在花部崛起的年月,也似春笋一般,纷纷破土而出了。如贵州侗族的侗戏,布依族的布依戏,云南白族的吹吹腔剧(白剧之前身),傣族的傣剧,以及分布在云南、广西两省的壮族的壮剧等。而15世纪便在西藏地区形成的藏剧,此刻已呈繁荣蓬勃之貌。它们各异的形态、风格,分明体现着自己民族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乾隆南巡——“花部”崛起的机遇
入清以后,康熙帝六次南巡,据其所称,是为了视察河工。“朕黄、淮两河,为运道民生所系,屡次南巡,亲临阅视,以疏浚修筑之法,指授河臣,开六塌以束淮敌黄,通海口以引黄归海”,但大半是为了安抚东南民心,以图社稷永固。所以,他一再告诫大臣及地方官,“毋得更以预备行宫供设御用,冒侵库帑,科敛阎闻”,“往返皆用舟楫,不御室庐,经过地方,不得更指称缮治行宫,妄事科敛。其日用所需,俱自内廷供御”。乾隆帝为政,有意效法乃祖康熙,即所谓“入疆考绩,或遵祖烈”,声称:“务从俭约,一切供顿,丝毫不扰民间”,“经过道路,与其张灯结鳏,徒多美观,不若部屋茅檐,桑麻在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过随处铺张,奢侈至极。仅以江北而论,徐州至扬州,不过数百里之遥,行官便建有好几处,所需木材多由东北长白山运至,耗费金银难以计数。
而且,乾隆帝所到之处,必有歌舞供奉。这是因为,“圣意颇好剧曲,辇下名优常蒙恩召入禁中,粉墨登场,天颜有喜,若一径宸赏,则声价十倍”。《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引孔子语谓:“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所以,凡乾隆“所驻跸之地,倡优杂进,玩好毕陈”,“扬州菊部之盛,本以乾隆问为最,其由于鹾商之豪华者半,而临时设备为供奉迎驾之养者亦半”,则道出真实消息。地方官绅、富商明知皇帝“恒以禁制倡乐为言”,但又深知其“嗜女乐”的底细,为了讨得皇帝欢心,曾进献“集庆班”、名伶荟萃的“四喜班”以及“训练之熟,设想之奇,当世无两”的如意班人行宫演出,所演剧目有《绣户传》、《西王母献图》、《华封人三祝》、《东方朔偷桃》等多种。其中,如意班主“所特制之剧场,能随御舟而行,其布置一切,与陆地上行宫无异,令皇上几不知有水上程”。另一戏班之表演则更奇,初则一鲜红可爱之蟠桃渐近御舟,忽又上升数丈,下呈根干枝叶之形。再则桃落巨盘之上,“若有人捧之献寿者”,后则桃开两面,各垂其半,中为一剧场,男女老幼数十人表演于场上,出“寿山福海”四字,最后由一光艳女子翩跹出场,上龙舟跪拜,献酒果等物。果然博得乾隆龙颜大悦。
其实,乾隆帝爱看戏,当是实情。著名文人赵翼曾在《蘑曝杂记》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谓:“内府戏班,子弟最多,袍笏甲胄及诸装具,皆世所未有。”他曾随驾秋季至热河行宫,亲见为庆贺乾隆帝生辰,连续演大戏十天之事,称:“所演戏,率用《西游记》、《封神传》等小说中神仙鬼怪之类。取其荒诞不经,无所触忌,且可凭空点缀,排引多人,离奇变诡作大观也。戏台阔九筵,凡三层。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两厢楼亦化作人居,而跨驼舞马,则庭中亦满焉。有时神鬼毕集,面具千百,无一相肖者。”乾隆二十六年,为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仅沿途所设置景物的准销银,即为七万八千余两。并安排许多承应彩戏:大班十一班,每班雇价二百两,计二千二百两;中班五班,每班雇价一百五十两,计银七百五十两,加之小班、杂耍、扮演彩戏的砌末添置、工饭零星费用等,竟用银达一万七千余两。甚至“演剧设乐”、经费报销,均由皇帝亲自过问,说明乾隆喜好戏曲,由来已久,并非仅仅发生在南巡之时。又据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载述:“每年坤宁宫祀灶,其正炕上设鼓板。后先至,高庙驾到,坐炕上自击鼓板,唱《访贤》一曲。执事官等听唱毕,即焚钱粮,驾还宫。盖圣人偶当游戏,亦寓求贤之意。”足见《南巡秘史》所述不虚。
乾隆既有此嗜好,当时“各处绅、商,争炫奇巧,而两淮盐商为尤甚,凡有一技一艺之长者,莫不重值延致。”加之“南巡时须演新剧,而时已匆促,乃延名流数十辈,使撰《雷峰塔传奇》,然又恐伶人之不习也,乃即用旧曲腔拍,以取演唱之便利,若歌者偶忘曲文,亦可因依旧曲,含混致之,不至与笛板相迕。当御舟开行时。二舟前导,戏台即驾于二舟之上,向御舟演唱,高宗辄顾而乐之”。而且,“自京口启行,逦邋至杭州,途中皆有极大之剧场,日演最新之戏曲,未尝间断”。淮扬当然更是如此。如此众多之戏班,究竟如何管理,则成了各类有关官吏所应考虑的问题,所以才有“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之事。不仅如此,他们还组织文士修改戏曲。据《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丁酉(四十二年,公元1777),“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及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总校黄文旸、李经,分校凌廷堪、程枚、陈治、荆汝为,委员淮北分司张辅、经历查建佩、板浦场大使汤惟镜。”黄文旸奉命“修改古今词曲”。又“兼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因得尽阅古今杂剧传奇”,遂以此为契机,撰就《曲海》(二十卷)一书。这恰说明,戏曲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艺术样式,已开始名正言顺地为官方所认可,由初始的乱而无序的民间之状态,已堂而皇之地步人皇室贵族的殿堂,成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即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共同追捧的对象。在以往,戏曲虽然也时而演出于王公贵族的宫室、厅堂,但似乎还未如此风光过。作为封建统治者来说,醉心于戏曲,自然是为了满足豪侈生活的需要,以求得感官上的愉悦,但在客观上却为戏曲的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为花部这一“才露尖尖角”的艺术“小荷”,提供了展示自我、完善并丰富自我的最佳契机。
仕、商运作——“花部”生存空间的拓展
地方戏以其浓重的乡土气,早就不为“文人墨客”所喜。明代著名散曲家陈铎,精通音律,有“乐王”之称,并曾撰有杂剧、传奇,是一个热心于通俗文学的风雅之士。但在他看来,流入金陵的“川戏”,不过是“把张打油篇章记念,花桑树腔调攻习”,“提起东忘了西,说着张诌到李,是个不南不北乔杂剧”。“也弄的些歪乐器”,“乱弹乱砑”、“胡捏胡吹”,加之扮相的不雅。“礼数的跷蹊”,无非是“村浊人看了喜”,只不过“专供市井歪衣饭”。上不得大台面,难以供奉官员府第。“新腔旧谱欠攻习,打帮儿四散求食”,显然对地方戏颇为轻视。然而,陈铎所云,也道出地方戏的一些特点,一是“不南不北”,恰说明当时的川剧并不严守南、北曲之宫调,仅取其上口、便唱而已。徐渭在论及“永嘉杂剧”(即南戏)时说,“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富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间有一二叶音律,终不可以例其余。”川戏“不南不北”何尝不是如此?恰体现出民间艺术的特色。其二是“村浊人看了喜”,恰说明川剧所搬演的剧作,内容活泼生动,贴合下层百姓心理,为普通民众所喜好。
至明代中后叶,随着昆山腔的流播,其影响越来越大,逐渐被尊为正声,时人目之为“时曲”。传唱北曲者渐稀,“有院本、北调不下数十种,今皆废弃不问,只剩弋阳腔而已”,然“弋阳腔亦被外边俗曲乱道”,改变了其原来的腔调。这说明弋阳腔在与其他戏曲声腔的竞争、碰撞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着“外边俗曲”以丰富、充实自身。由此可知,其声腔体系不是封闭、保守的,而是以开放的态势,不断融汇相邻艺术之长,为其自身的成长注入活力。这或许是弋阳腔一变再变,某些唱法至今仍保留在全国许多剧种中的重要原因。清代至康熙时,宫廷仍在唱弋阳腔,不过用该腔演唱的剧目,仅占十分之三,远远比不上昆山腔。尽管如此,苏州织造员外郎李煦,为“博皇上一笑”,欲“寻得几个女孩子”。“寻个弋阳好教习,学成送去”,说明弋阳腔在清初内廷,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稍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雍正帝禁止官吏蓄养优伶,大半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他认为,外官蓄养优伶,“非倚仗势力,扰害平民,则送与属员乡绅,多方讨赏,甚至借此交往,夤缘生事”,故称“家有优伶,即非好官,着督抚不时访查”。督抚若访查不力,或故意循隐,将“从重议处”。乡间演戏,或禁或准则区别对待。乾隆初年,所禁者乃充满“媒亵之词”的淫戏,“忠孝节义”、历史掌故、神仙传奇则不在禁之列,且“凡各节令皆奏演”,并不时用演戏招待域外来宾,故“内廷内外学伶人总数超过千人”。但对地方戏却采取压制之政策,称:“城外戏班,除昆弋两腔,仍听其演唱外,其秦腔戏班,交步军统领五城出示禁止。现在本班戏子,概令改归昆弋两腔。如不愿者,听其另谋生理。倘有怙恶不遵者,交该衙门查拿惩治,递解回籍。”直至嘉庆初年,“苏州钦奉谕旨给示碑”尚称:
乃倡有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者,非狭邪蝶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此等腔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辗转流传,竞相仿效。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旧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
在此前后,查禁地方戏,每每出现于各级官吏的奏折中,如两淮盐政伊龄阿于乾隆四十五年所上奏折:
查江南苏、扬地方昆班为仕宦之家所重,至于乡村镇市以及上江、安庆等处,每多乱弹。系出自上江之石牌地方,名目石牌腔。又有山陕之秦腔,江西之弋阳腔,湖广之楚腔,江广、四川、云贵、两广、闽浙等省皆所盛行。所演戏出,率由小说鼓词,亦间有扮演南柬、元明事涉本朝,或竞用本朝服色者,其词甚觉不经,虽属演义虚文,若不严行禁除,则愚顽无知之辈信以为真。亦殊觉非是。
剧坛争雄——完善自身的良机
乾隆之时,是花、雅争胜的时代。这在多种文献中均有反映。剧作家蒋士铨在所著《西江祝嘏·升平瑞》一剧中,叙及提线傀儡班将演出于江西南丰。当别人问及“你们是什么腔,会几本什么戏”时,班主回答:“昆腔、汉腔、弋阳、乱弹、广东摸鱼歌、山东姑娘腔、山西卷戏、河南锣鼓戏,连福建的鸟腔都会唱,江湖十八本,本本皆全。”蒋氏为江西铅山人,所言或有所据。清人徐孝常,在为“江南一秀才”张坚《梦中缘》传奇作的“序”中亦谓;“长安梨园称盛,管弦相应,远近不绝;子弟装饰,备极靡丽;台榭辉煌,观者叠股倚肩,饮食者吸鲸填壑。而所好惟秦声啰弋,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朋然散去。”说明花、雅之争胜,非扬州一地个别现象,已波及全国许多地区,且昆腔已呈衰微之势。尽管如此,由于最高统治者的保护和扶植,昆山腔的正统地位,依然没有动摇。对花部持有偏见者,不乏其人。即以张坚而论,“为文不阿时趋尚。试于乡,几得复失者屡屡”,乃“穷困出游”,郁郁寡欢。然而,当有人把其所作《梦中缘》购去,“将以弋阳腔演出之”时,他却“大怒,急索其原本归,曰:‘吾宁糊瓿。’”便很能说明问题。
当然,花部戏曲的逐渐精细化。与艺人同文人的主动合作、文人的广泛参与有关。花部剧作,“问用元人百种戏”或明传奇,但在情节、排场等方面做了大量改动,已远非本来面目。如《打店》,很可能是从沈琛《义侠记》中“释义”一出化出,但加大了插科打诨与调笑,使喜剧色彩变浓,显然是经过了文人的再加工。扬州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各类书院亦甚多。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三载:“扬州郡城,自明以来,府东有资政书院,府西门内有维扬书院,及是地之甘泉山书院,国朝三元坊有安定书院,北桥有敬亭书院,北门外有虹桥书院,广储门外有梅花书院。其童生肄业者,则有课士堂、邗江学舍、角里书院、广陵书院。训蒙则有西门义学、董子义学。”这些教育机构,培养出一大批文学人士。乾隆之时,著名文士如朱孝纯、姚鼐、王文治、张宾鹤、朱贫、罗聘、张道渥、陈祖范、杭世骏、周升桓、蒋宗海、金兆燕、蒋士铨、赵瓯北、王嵩高、李保泰、谢溶生、任大椿、洪亮吉、孙星衍等,均曾在此留恋不去,或寄居于此。扬州一代成了文人的渊薮。马日瑁、马日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江春的康山草堂,亦是延揽文人之地。
诗词唱酬,看戏赏曲,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文人观赏戏剧的眼光,一般都比较苛刻,这为花部戏班在名优、名班林立的扬州生存带来了难度,势必在演技上下大力气,何况文士中不乏赏曲名家。如“好诃曲”的程志辂,“凡名优至扬,无不争欲识”。“山中隐君子”詹政,能指出戏班“数日所唱曲”,“某字错,某调乱”,令“群优皆汗下无地”。文人对戏曲活动的参与,使得花部表演艺术渐趋提高,则是不争的事实。
由上述可知,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兴盛与发展,都是多种社会条件、文化因素合力的结果。花部当然也不例外,是扬州特有的地域文化沃土,培育出这枝文艺新芽。扬州富商众多,又是文人渊薮,二者之间交往频繁。如此一来。使得商人在追逐刀锥之利的同时,又多了几分书卷雅气。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士们在舌耕笔播的同时,对商人习气以及世风流俗,由排斥、拒纳转而为宽容与认可,眼界上开阔许多。富贾与文人的融汇与互动,促成了扬州一地兼收并包、较为开放的社区文化。“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一定会挑选合乎他们性格的娱乐”。正如有人所说:“客观形势与精神状态的更新一定能引起艺术的更新”,花部戏曲基本形态的形成,正与这种特殊的社区文化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