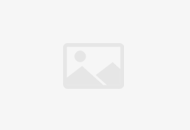在1914年的马恩河战役之后,协约国和同盟国在法国北方和比利时一角的战线上陷入了僵持状态。法国大臣推荐采取“外围战略”的办法打破僵局。
1914年11月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提出凭借英国海军的实力打开达达尼尔海峡登陆,然后在加里波利登陆,直取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把土耳其逐出战争。一方面又减轻俄罗斯高加索山战线的压力。得到君士坦丁堡控制的金角海就可直通黑海,支援血战的俄国军队。并且,希望借此开辟南线,攻打奥匈帝国。此设想,在战略上固然相当高明,但实行起来却搞得一团糟。
1915年1月2日英国政府接受了尼古拉二世的请求,决定在达达尼尔海峡展开一条新战线。
加里波利之战地形图
英法两国投入战役的共计有62艘战舰,以及大量辅助船只,并指定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萨克维尔·卡登(Sackville Carden)上将负责指挥这次战役。舰队从2月19日开始炮轰达达尼尔海峡。1915年3月18日,16艘军舰企图强行闯入狭窄的海峡通道, 4艘军舰触发水雷,舰只慌忙撤退。
在陆地上,土耳其军队在遭受突然袭击的情况下,纷纷丢弃阵地向内陆退却,英国突击部队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率先冲上海岸。至此,德国军事顾问奥托·冯·赞德尔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已洞悉对方计划中的加里波利登陆战,火速调动军队至战区。土耳其军队掘壕坚守,依据半岛复杂的地形建立了强大的防御体系,又在该地集结炮兵部队。
在英法军队准备扩大战果时,隐蔽在阵地中的土耳其士兵一起开火,把正在攀登悬崖的英军也打了个措手不及。
1915年3月3日,联军的首轮登陆行动宣告失败,卡登上将也被当作伤员送回英国。
盟军发现单纯依靠海军无法夺取海峡之后,判断一定要以陆军占领加里波利,才可得到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协约国在埃及和希腊群岛仓促中集结了一支远征军,七万八千名来自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和法国的士兵陆续抵达战区。其主力由当时在埃及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组成,即“澳新军团”(ANZAC)。英国兵部大臣赫瑞修·基钦纳(Horatio Kitchener)命有“诗人将军”之称的英国陆军上将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负责指挥这次战役。
与其对阵的是由冯·赞德尔斯率领的土耳其新编第五集团军,有八万四千人。当协约国远征军抵达时,兵力已被对方超过,土军居高临下,火力又占压倒优势。
根据计划,英军和澳新军团在同一天,分别从两个不同登陆点上岸,英国军队从海丽丝岬(Cape Helles)登陆。在英国登陆之前,澳新军团先在更北面靠近伽巴帖培(Gaba Tepe)的海滩登陆。
1915年4月25日夜,在掩护舰队实施炮火准备后,协约国部队同时展开登陆行动。由于澳新军团士兵大多没有接受过夜间登陆训练,再加上对半岛地形一无所知,错误地登陆在目标以北的一个无名小湾(今澳新军团湾)。同一天,英国和印度部队在海丽丝岬遭到土耳其猛烈火力攻击。法军在海峡对面,达达尼尔亚洲一边登陆,但第二天撤退加入英军。虽然建立了滩头阵地,登陆军根本就无法把部队有效展开,实际上陷入了不稳固的、难以防守的立足点。
土耳其军队在穆斯塔法·凯末尔上校(后来“土耳其之父”阿塔土克)的指挥下,随即进行了猛烈的还击。经过一夜的混战,双方死伤惨重,已登陆的1.6万名澳新军团士兵在土耳其军队炮火的压制下,被困在临时掩体中动弹不得,接下来的几天,双方陷入了僵持的局面。
1915年5月1日,土耳其军队大举反攻协约国部队最南面的一个登陆场。在战斗中,英国战列舰歌利亚号(HMS Goliath)、凯旋号(HMS Triumph)和威严号(HMS Majestic)相继被击沉。结果英国撤离了大批舰只,这样一来,登陆部队便失去了海军的支援,也失去了火力优势。
1915年5月6日至8日,协约军向克里希亚(Krithia)进攻,死伤惨重,最终失败。19日土耳其沿着整个澳新军团前线发起反攻。士兵在一连串自杀式冲锋中战死。澳新军团无法占领预定的山头目标,他们被困守在一条从海滩到前沿不过400米的单薄的阵地上。
随着夏季的来临,上坡上遍地尸体,带来痢疾、腹泻和肠热等疾病。半岛上的澳新军团士兵因气候不适导致非战斗减员持续增加。但协约国为了赢得此次行动的胜利,又调配了3个师的英军前往半岛。
与此同时,冯·赞德尔斯也在拼命集结土耳其军队,准备迎接新一轮的进攻。
1915年8月6日,新一轮的登陆战在澳新军团登陆场西北面的苏弗拉湾(Suvla Bay)拉开。配合这个计划的两场战斗在独松(Lone Pine)和尼克山谷(The Nek)展开。这次行动由英国陆军资深将领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Frederick Stopford)将军指挥,由于土耳其人在苏弗拉湾的防守比较薄弱,英军在登陆时未遇到太多抵抗。可惜的是部队上岸后未能及时扩大登陆场、巩固滩头阵地和向内陆推进占领制高点,宝贵的战机再次被错过了。冯·赞德尔斯紧急从其他防线抽调了近2万土耳其军队抵达苏弗拉湾,抢先在萨里巴依尔山脊设置了一道临时防线。凯末尔亲自领土军成功遏制了协约国军队前进的步伐。
9月,战事又开始陷入僵局。
1915年9月,汉密尔顿被召回并被解除了指挥权,察尔斯·门罗(Charles Monro)将军接替了他,但协约国军队的伤亡人数仍与日俱增。初冬寒冷,许多兵士患病,严重冻伤迅速在部队中蔓延,超过16,000人冻伤,有人甚至冻死。
1915年11月23日,国防大臣基钦纳视察战场后,不得不下令按阶段撤退。9万军人秘密撤离加里波利,而土耳其人完全没有发觉。整个战役中,撤退是最成功的行动,伤亡不到10人。《福斯报》军事记者发出的通讯写道:只要战争不息,苏弗拉湾和澳新军的撤退,将在所有战略家眼中,成为前所未有的杰作。
1916年1月9日,当最后一名澳新军团士兵离开海滩后,这次一战中最大的登陆战也就正式宣告彻底失败。
史学家分析此次作战,计划疏漏,指挥不当,配合不力,导致伤亡惨重。其中,失败很大原因归咎于指挥者的优柔寡断,正如一名英国历史学家所言:“这是一个正确、大胆而有远见的计划,但却被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错误给断送了。”
协约军:44,072战死,97,037负伤
英国:21,255战死,52,230负伤
法国:约10,000战死,约17,000负伤
澳大利亚:8,709战死,19,441 负伤
新西兰:2,701战死,4,852负伤
印度:1,358战死,3,421负伤
纽芬兰:49战死,63负伤
奥斯曼帝国:86,692战死,164,617负伤
土耳其政府建立加里波利半岛国立历史公园纪念加里波利之战而死的50万士兵。公园里建有纪念馆、纪念碑和墓地。
今天,加里波利半岛昔日战场,许多已经变成了农场。惟独澳新军团湾模样基本没变,成为了土耳其旅游景点。
加里波利之战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想象中,代表了两国的国家特征:英勇顽强和队友情谊(mateship)。因此4月25日,澳新军团登陆的日子,被定为澳新军团日,为纪念加里波利之战牺牲的联合军团将士。
今天,澳新军团节已成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重要的节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