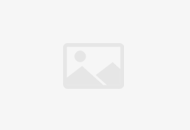17世纪中叶张献忠和清军先后攻入四川。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西进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在大西政权前期,虽手段强硬,但军纪尚可。后因四川各地明朝势力反抗强烈,张献忠于是决定杀戮报复。其死后,清军势力开始介入。康熙三年(1664年)清朝集合十万大军围剿农民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在川地多杀戮。等待清军平定四川大部时,镇守云南的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起兵反清,四川再次成为战场,八年之后,清军彻底平定四川。经过数十年的动乱和战役,使得四川人口大减。
过程崇祯十七年,张献忠西进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在大西政权前期,虽手段强硬,但军纪尚可。后因四川各地明朝势力反抗强烈,张献忠决定杀戮报复。
南明时期的四川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汪兆麟献策屠蜀。次日,屠城成都,先杀男子,后逼妇女投江,被屠戮者不计其数,《纪事略》中说“不下四五百万,实际数不可考”。不久,又以“特科”的名义,骗四川的乡绅、士子、医卜僧道杂流到成都,后全部屠杀,被杀者万余人。顺治三年(1646年)年正月,大杀大西军中的川籍士兵,除十四岁以下者全部尽杀。该年上半年,派兵分剿成都府属三十二州县,定例每杀一人,剁两手掌、割两耳及一鼻解验,准一功,妇女四双手准一功,小孩六双准一功。直至五月各地剿杀部队才全部回成都。
顺治三年(1646年)春,张献忠在彭山江口大败于明军杨展,败退成都。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明总兵曾英进军成都,张献忠遂弃成都,向川北转移。由于受到进剿追击,张献忠于是将成都劫掠一空,另有一说说张献忠在撤军时,嫌士兵太多于是大戮士兵,并杀尽军中随军妇女,但此说和其他文献想矛盾,较不可信。
当时“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圣教入川记》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张献忠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到他临死时只有25人”。
争议对于张献忠“屠川”之说,清朝时的书籍中,其可信度有些值得怀疑,有一些历史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史料多半出自清朝的官方正史和御用文人,有严重的污蔑、栽赃的倾向。
?其一,攻占四川意图。
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既可出汉中定西北,又可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民众而自毁长城。
?其二,安抚当地百姓。
1644年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范围
以张献忠经营四川的第一年情况来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实的。1644年,张献忠进军成都时,明朝守土官员曾问张献忠入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团结所有有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打击的对象仅限于与大西政权为敌的官绅,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他在攻打泸州的檄文中说:“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失。”
保存至今的大顺二年(1645)《大西驳骑营都督府刘(进忠)禁约碑》郑重声明:“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不许擅自招兵,扰害地方;不许往来差舍擅动铺递马匹兵夫;不许地方武职擅受民词;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不许无赖棍徒具词诈告,妄害良民;不许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违者按碑律斩杀。这是张献忠起义军注意纪律的铁证。
与张献忠接触频繁的西方传教士曾统计过,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于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识分子,在张献忠攻克成都后,或“入学”,或“习举业”,以至于当大顺二年“开科取士”时,“应诏者不下数千”。
如果张献忠入川后发动大规模屠蜀或镇压官僚士子事件是真的话,上述原明官吏转到大西政权寻求保护,或是知识分子在新朝积极考取功名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就是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其三,“七杀碑”的传说。
例如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清政府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是,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找到了一块张献忠立下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是劝人畏天行善的,根本就没有一点杀气。而某些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其污蔑、泼粪之意,不言自明。
?其四,当地人自发祭拜张献忠。
在梓潼七曲山大庙,是中国第一座文昌帝君庙。奉祀主神自然是文昌帝君张亚子,但在大庙的风洞楼上还塑了一尊张献忠的绿袍像,附近还有有一座张献忠家庙。每年二、八月时,梓潼居民都要到塑像前参拜一番。当地传说是明朝崇祯年间,官逼民反,张献忠领兵对抗朝廷,到了梓潼后,杀贪官、开米仓,解决百姓长期的缺粮之苦,因此虽然朝廷大举围杀张献忠,四川百姓对于张献忠却有拥戴之心。
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砸毁,其后,又有人重塑,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张献忠如果屠蜀,当地百姓为何对他如此崇拜。
?其五,清朝“文字狱”的下被毁的真实史书,
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居御林院编修。他们的书有多大可信度值得怀疑。
而官方编纂的《明史》这部正史都漏洞百出,先是记载蜀地有三百余万口,后又记载张献忠杀了“六万万”蜀人。
?其六,张献忠死了十三年后,清廷才平定四川。
1646年,即清人入关后第三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中箭身亡后,满人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用了残酷的屠杀来征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再确凿不过的证据。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进攻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0年,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川境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千里已无人烟的四川,又何能抵抗清军十多年。
?其七,被杀人数的肆意夸大。
《续编绥寇纪略》和《明史》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六亿)人,这数字明显夸大,当时的中国总人口还不到一亿,这些事实说明清政府的宣传存在明显夸大的成分。然而也有人指出“六万万”的意思,其实就是六十万。
尽管历史上农民起义有乱杀的现象,但张献忠屠杀到四川只剩下6万人是不可想象的。
对此,《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有如下论述:
“《续编绥寇纪略》所记的张献忠起义军在川杀人数,绝不可靠。由此推想,旧史书上述几起张献忠起义军杀戮事件的记载,夸大渲染之处肯定存在。但是,关于上述杀戮事件,有多种史书加以记载,而且除了细节的差异外,基本情况大体相同,这说明这些事件应是确有其事。狭隘的地域观念,使他对四川人产生偏见,从而不仅杀了明朝残余势力,也杀了许多一般绅士,更杀了不少劳苦群众,这便使这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反人民性。由于张献忠之在四川大杀戮,具有反人民性的一面,这便使之严重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张献忠之大杀四川人,成为其后来遭到丧命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
“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
此外,将屠川责任全推给张献忠一人也是不合理的,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烬馀录》记载:
“今统以十分而论之,其死于献贼(张献忠)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及二,其一则死于病也。”“献贼”即张献忠,“姚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圣教入川记》却率直地写道:
“张献忠灭后,旗(清)兵在川,一时未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年。迨至1660年(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1681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由上述可见,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之“人祸”,实是张献忠、姚黄农民武装、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叛军等战乱共同肆虐之结果。此外,还有大旱、大饥、大疫、虎害。
平反1980年3月3日至3月6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邀集有关的史学工作者和专家,举行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学术讨论会。会上讨论了张献忠在四川“杀人”问题的真相,张献忠在明末清初农民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张献忠失败的原因等三个问题。到会同志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各抒己见,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正确评价张献忠,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到会同志一致指出,过去清廷统治阶级把张献忠诬蔑为“杀人狂”、“杀人魔王”等等,流毒既广且深,特别在四川留下的恶劣影响更不容忽视。至今无论城市、乡村,举凡四十岁以上的四川人,大多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所谓八大王“剿四川”的传说影响。
背景
清军在四川也是乱杀。清军平定四川2年后,清军因镇压陕西、山西起义,无暇全力顾及四川,1648年四川复反,清军又出兵围剿。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揭,给清廷奏章说入川的清军将领乱杀无辜,要不屠城,要不就把男的杀光。
张献忠死后,主要余部由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等率领南撤,经重庆、遵义,再到云南,于是四川本地各地军阀割据。入川的清军,先后在豪格、鳌拜、吴三桂、墨尔根、李国英、高民瞻的统领下,一方面镇压农民军,一方面与明朝军队交锋。
各军阀名义上效忠南明永历政权,互相之间却征战不休,连年征战更加加剧了四川的惨况,后孙可望又回兵平四川征讨各军阀使四川安定下来,川地生产逐渐恢复。1652年,陕西、山西起义已定,清廷派吴三桂重征四川,吴三桂平四川忠于明朝各军阀,击败南明蜀藩刘文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陷渝城(重庆)后,才算彻底平复四川,此间多方势力反复争夺使四川人口再次大规模流失。
三次屠蜀
清军对人民的镇压非常残酷。在清军与残明军队争夺攻伐的过程中,广大人民也颇受其害。
总的说来清军在四川大规模的屠杀破坏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领兵进入四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第二次是康熙时期为了镇压夔东十三家农民军;第三次是平定三藩之乱。
(1)清军首次屠蜀(顺治三年1646年—顺治十六年)。
豪格率领清军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于西充袭杀张献忠。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王先谦在《东华录》如是记载“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依据这则史料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数万级”都是大西将士。然而在《清史稿》中却有不同的记载:“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馀所,斩首数万级。”
表面上看两则史料并无太大不同,区别只是《东华录》中说清军“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而《清史稿》中则是“平其垒百三十馀所”。但仔细分析其中却有争议:张献忠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清军偷袭,而且张献忠率军北上目的地是陕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固守西充,更不可能有意识的针对清军修筑大量的堡垒和清军打阵地战。
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清军平的“垒百三十馀”并不是大西军队所修筑的,而是那些在川北与张献忠对抗的乡绅地主所领导的堡垒。清军为了粮食而进攻这些堡垒,张献忠放弃成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川西因战乱灾荒而缺粮,入川的清军同样面临这一问题,那些堡垒里恰恰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一点从清军在简阳地区的掳掠可以得到印证“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
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战死,清军“斩首数万计”。清军打败大西军之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如前所述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较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这里却发生了巨变。
顺治四年(1647年)春,李国英率清军入成都,后留其将张德胜守之,发生内讧。明降将齐联芳杀张德胜,张的部下“多遁回川北”,而齐联芳及其部下一千多人,亦遭清军邀击被杀。于是,“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不仅如此,清军还因粮食缺乏,用残酷刑罚,强迫人民纳粮,如顺治四年清兵为南明军队打败,败退过简州时,清军“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
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清军因孤军深入,不得不撤出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由于四川军民的反抗及粮荒,同年年底,清军不得不放弃四川的大部分控制区,向保宁集结,在撤退过程中清军竟大开杀戒,大肆屠杀平民百姓,“十一月,(南明军)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而后,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
清军甚至还大量地以人为粮,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清总兵马化豹的《塘报》中说,他带领的清兵攻打樊一蘅、杨展等部明军,“战守叙府(宜宾)已八个月,叙属府县止傕(催)稻谷四十八石、粗米九石,何以聊生?嗷嗷待哺。所部官兵俱将骡马宰吃,日逐禀泣,难堪度日。凡捉获贼徒,未奉职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本职若敢妄言,难泯官兵之口。”这是清军将领的军情报告。地主阶级诬说农民起义军以人为粮,原来,以人为粮的正是他们自己。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进攻中江、潼川(三台)、射洪,“斩获无算”。
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在川北进攻民寨打粮时还是如此残酷“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无数,……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
顺治九年(1652年),清军在保宁“擒斩(王)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攻开州(开县),“阵斩贼二千有余”。
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高民瞻攻成都,起义军南撤,清军“追至新津河,阵斩及溺死无算”。吴三桂军驻川南时,也是“骄横日甚,而部下尤淫杀不法”。至此清军才占领四川大部分地区。
从顺治四年至此的十多年里,满、汉地主在四川大量残害人民,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清将李国英入四川后,接纳阆州生员刘达为其幕僚,并派他到西北去办买战马,这时,他离开了阆中。顺治十五年,刘达返川交差、回到阆中故里后,给李国英的一封信中,对比了离川和回川前后目睹的情况。他写道:“返乎三巴,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涂。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篙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这些变化,都是在张献忠牺牲之后,都是满、汉地主在四川的残暴罪行不能算在农民起义军头。
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
?康熙时期
(2)清军二次屠蜀(康熙三年)。
1658年清军占据四川大部
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四川平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1651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然而康熙三年(1664年),二十万清军的大围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四川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事后清朝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
(3)清军三次屠蜀(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的第三次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军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就是军纪甚差。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整个四川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这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难。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这时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康熙酋长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
1659到1664年清军围剿奎东十三家
有了康熙的纵容,入川的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屠杀四川平民百姓。据康熙十九年(1680年)富顺新任县令钱绍隆《详请禁病害文》中所载:“……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里甲胥役具皆潜逃不知去向。职随出告示招抚,无如一路逃兵来牵宰耕牛,攫取鸡豚,稻米豆谷,悉皆抛散……即至极幽极深之地,无处不到。如相近内江一路,……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兵丁驾船抢掠,……一路人见此辈带刀前来,无不骨拆心惊魂胆俱丧也。又泸州,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间,庶几可持无恐。无如兵之所过,遍山搜寻。其妇女望见惊走,媳弃其姑,母弃其子,童稚不能相随者弃置山谷,越日走视,为虎所伤而死。……(妇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尸在草野,经月不收……此皆历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
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后来雍正自己在一段话里都承认清军屠杀平民对整个人口损失的巨大影响,在雍正谈到清初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除了把责任归咎到流贼头上,也不得不承认清军的疯狂屠杀行为。
南明军其实南明除了杨展是真正为了四川人着想,只可惜杨展因为他管辖的地盘逐渐富裕,在1648年被袁韬和武大定杀害。
早在张献忠牺牲以前,南明官军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拼命的反扑,残酷屠杀人民。史载明军“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劫杀,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
1846年南明军和大西军势力范围图
顺治三年(1646年)底,张献忠牺牲后,四川大部分地区为残明官军占有。他们变本加厉,镇(审核)压革命,搜杀人民,并且,互相攻伐,争权夺利,扩充地盘,拥兵自雄,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苦难。顺治四年(1647年)六月,南明官军王祥部总兵王命占领顺庆,“其始也,每家给免死牌一张,需银若干两。其继也,每牛给牛票一张,需银若干两。未几,而牵其牛,掠其人,掘其粮,焚其室,胥西南之民而兵之。”
顺治六年(1649年),南明官军曹勋部驻雅州,“其兵亦不易得食,于是纠合焦英等队外掠西道,内掠雅边,豆、麦、高粱搜括无一粒。遗黎草根、木皮充腹,迨尽,僵尸满路,城乡至显设卖人肉汤锅。”故当时亦有“宁遇恶虎,不遇曹部”之谚。
至于残明官军之间互相争夺中,对于人民的扰害,清初杨鸿基的《蜀难纪实》中说得相当具体。它写道:“(残明官军)闻贼北去,相与倡言恢复,牵率而西。凡贼杀戮之余,恣其拷掠。方至简(简阳)、汉(广汉)间,不虞尚有余贼,回兵一击,大溃而奔,不敢复西。而惟盘踞于资、内、富、隆、沪、合之间,日以挞粮为名,四出抢掠,其难更酷于贼。……每得一人,榜刺炮烙,必得财物而后已,……故民虽免于兵刃而死于拷掠者十常八九也。时蜀土不耕已二年余,粮罄尽,民惟拾穞谷、采野蔌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又说:“时蜀疆无寇,向之仗言恢复者皆出而据土自雄。于是,杨展据嘉定,省东州县、上下川南皆其属,惟永、泸不与焉;王祥据遵义,以津、合、彭、黔为边境,而时扰于境外,侯天锡据永宁(叙永),马应试据泸卫,而时往来于泸、富之间,曾英部将余(于)大海、李占春据涪州之平西坝,上而长垫,下止醴都,川北则以近清,而不敢问,其忠、万,则忠州世弁谭文、谭宏及谭诣号三谭所有。其他聚一乡、保一砦,或孤立自守,或臣附于他人者,固难仆数也。使其各保境安民,积粮养士,以待时清,则蜀难从此亦可止矣。无如此曹贪乱乐祸,不肯少悛,日寻干戈,忍相吞噬。当此千里无烟之日,孑遗落落,值其蹂躏,呼天罔应,入地无门。”杨鸿基,是顺治、康熙时四川富顺县人,他的这一段概括的描述,正是当时残明官军在四川残害人民的真实缩影。
当地地主武装当地地主武装也是这样,如雅州“黎神武等所为,残忍妄诞,凡有俘获及挟仇相害者,但云从贼,无不手刃之。”这些地主武装,在其辖区内大肆掠杀人民,如顺治二年十一月,南明监建黎军范文光“驻节雅州”,“分兵劫掠”,以致“雅民剥床见肤,各星散逃去”,“又纵兵掳掠,雅安民遭害甚惨”,所以当时有“宁逢赤眉,不逢文师,宁遇恶虎,不遇曹部。”之谣。在人民看来,农民起农民军(“赤眉”)比地主武装好。
为了争抢粮食,一切仁义道德都已经不存在了。有个冯氏家族写了本《冯氏历乱录》,在书里对当地摇黄土军任意肆虐和清军开道杀人都有描写。清军攻周时缝草便杀,据欧阳直的《蜀乱》记载,摇黄土军杀人,吃人之事也干不少,在一座庙里,他们抓大头的小孩,将其四肢绑住,用头撞钟,看其被撞得脑浆迸裂以此来取乐,是“更甚于献忠”。张献忠的军队是支有军纪的军队,所干之事都是有目的的,而摇黄土军就是毫无纪律的土匪了。由此可以看出,张献忠所毒害的主要在川西一带,川南是南明和摇黄的地盘。随着清军入川,他们之间互相争夺,为了地盘和粮食,导致川南“孑遗者百无一二”。
其他农民军而其他一些农民军残余力量例如摇黄军也在四川各地屠城。劫掠妇女,残害老幼,使得满地尸体。
战乱的同时还有天灾,而实际上四川发生的自然灾害无论涉及的区域面积,严重程度还是持续时间同样远远低于陕西、河南。
天灾清同治十年的《仪陇县志》载:“仪邑自明季之乱,几至靡有孑遗,其逃在山谷者,又值饥馑频仍,人相食,继以虎灾,道无行人,昼常扃户。”
瘟疫《蜀碧》:“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死者朽卧床榻,无人掩葬”。顺治五年(1648年),内江“瘟疫大作,人皆徙散,数百里无人烟”。同年,川北又遭大旱,饿死者日无计。
《铜梁县志》载1868年,该地“瘟疫四起,染者呕吐交作,腰疼如断,两脚麻木愈二三时之毙”。
虎患欧阳直的《蜀乱(蜀警录)》记四川虎患,“蜀中升平时从无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内江奔溃,余途次草中,月下见四虎过于前。又于叙南舟中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一虎浑身纯白,头面长毛,颈上披须,长径尺。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虎之口,而蜀人几无噍类矣。嗟乎!死于贼与饥也,犹曰人死于虎也,非天乎!。”
彭遵泗《蜀碧》载:顺治初年四川“遭乱既久,城中杂树蓊郁成林……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顶逾城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毙即弃去,不尽食也。白昼入城市,遗民数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经数日,而一县之人俱尽残者”。
顺治七年四川地方官员向朝廷奏称,顺庆府“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奈频年以来,城市鞠为茂草,村疃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噬。……据顺庆府附廓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506名,虎噬228名,病死55名,现存223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现存32名。”
沈荀蔚《蜀难叙略》载:顺治八年春“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乃闻川东下南尤甚。自戊子(顺治五年)已然,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若取水,则悉众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终有死者。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谨疫疠者,又尽于虎矣。虽营阵中亦不能免其一、二。”
乾隆《富顺县志·卷5》记载,清初“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不见一人驰逐之。其胆亦张,遇人即撄,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焉。残黎之多死于虎”。
道光《綦江县志·卷10》记载,綦江“群虎白日出没,下城楼窥破残人户。……行者虽五、七同群,执器械,前后中间必有一失。”
《明史》记载是六亿人被害,而《后鉴录》记载是七亿人。
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里说从崇祯初年开始,四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685万人口死亡,残存的居民仅50万左右。
其实除了《后鉴录》之外,其他的资料很多都并没有将全部责任推给到张献忠身上,如《蜀龟鉴》记载: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四川南部死于张献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于瘟疫、虎灾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遗之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遗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明朝军阀的屠戮平民、清军的滥杀无辜,特别是清军(包含吴三桂),比南明,张献忠,摇黄土军和各路强盗土匪更加残暴,再加上灾荒,瘟疫,虎患,人吃人,逃离等天灾人祸,才是导致川人减少的真正原因。
明末清初在中国各地发生的动乱之中,尤属四川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蜀这一词就很清楚的说明了当时四川在人力、物力方面所遭受的惨重损失。
连年兵荒马乱导致的生产大面积停顿,人民大批量地逃亡,都是导致四川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人口锐减的原因,按顾诚说法,“直到张献忠牺牲,大西军转入云贵时,四川遭受的破坏还是比较有限的”。
屠蜀使四川的经济与文化遭到摧毁,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战乱,永远无法准确统计,长年的战乱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百姓弃田舍逃亡,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川人死于饥馑、瘟疫又倍于刀兵。[1]
屠川事件几乎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了四川的文化与生产力。尤其是对四万贡生——中国文明与文化传承者的屠杀,给后人留下了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的空白——从此再无四川人。
为了恢复四川经济,清初鼓励全国各地向四川移民,于是开始了长达100余年的“湖广填四川”。不过也有人指出湖广填川是假的。[1]
雍正帝: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人民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
孙祚民:统治阶级把这一事件称做“蜀祸”,以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诋毁不遗余力,直至很久以后,在人民中间还存留着某些影响。
黄位东:明末清初期间各方势力在四川进行疯狂屠杀,将天府之国变为人间地狱,给时人带来了难以抹去的伤痛。
胡昭曦: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请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