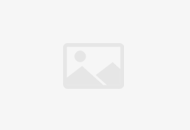编者按:1950年代,一名美国医生为观察癌症是否会传染,给在押犯人和不知情的病人注射癌细胞,事件引起公众对医学伦理的关注,推动了伦理规范的出台,确立了知情同意权和伦理审核委员会,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对受试者权益的保护并没有像科学家担忧的那样阻碍科学进展。
海拉细胞,来自海瑞塔·拉克斯的癌症细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以无限制复制的“永生”细胞。
海拉细胞像雨后春笋似的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不断增殖,病毒学家切斯特·索瑟姆(Chester Southam)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要是科学家被海瑞塔的癌细胞感染了可怎么办?盖伊和其他科学家已经证明,大鼠注射了活的海拉细胞会长肿瘤,人难道不会吗?
科研人员呼吸着海拉细胞周围的空气,整天把它们从一个小瓶移到另一个小瓶,有可能不小心碰到它们,他们甚至就在海拉细胞旁边的实验桌上吃饭。有个科学家用海拉细胞研制出一种对抗感冒病毒的疫苗,他给400多人进行了注射,疫苗不纯,里面还含有少量海拉细胞。没人知道海拉细胞或者其他癌细胞会不会让人患上癌症。
“可能有危险,”索瑟姆写道,“研究过程中不小心注射,或者在注射抗病毒疫苗时带进了残留细胞或者细胞代谢物,都有可能引发肿瘤。”
索瑟姆是一位颇具声望的癌症研究专家,他还是美国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Sloan-Kettering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病毒学系的负责人。他和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癌症是由病毒感染或免疫系统缺陷所致。索瑟姆决定用海拉细胞检验他的理论。
1954年2月,索瑟姆在针管里装满掺有海拉细胞的盐溶液。他把针头扎入一位女士的大臂,这个人刚因白血病住进医院。接着,他缓缓推动针柄,大约500万个海拉细胞随之进入女士的体内。注射的部位鼓起一个小包,索瑟姆换了个针头,小心地在旁边点了个小墨点留作印记。这样不管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后,他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注射部位,检查海拉细胞有没有引发癌症。用这种方法,他把恶性肿瘤细胞注射到十几位癌症患者体内,然而给他们的解释却是测试免疫系统,对真相绝口不提。
注射完成几小时之内,病人大臂开始红肿;五至十天后,注射部位出现硬瘤。索瑟姆切下一些瘤子,检验里面是不是癌细胞,但却有意留下一些,好看看病人的免疫系统是否能抗衡,或者相反,这些癌细胞是否会扩散。不出几个星期,有的瘤子已经长到直径两厘米——当初海瑞塔开始接受放射性镭治疗的时候,体内癌变就是这么大。
索瑟姆最终为接种者切除了大部分硬瘤,其他的几个月后也自行消失了。可其中的四位病人不久后又肿瘤复发。索瑟姆不断为他们切除,但肿瘤却一次又一次地长起来。一位病人的癌细胞甚至扩散至淋巴结。
但这些病人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患有癌症,为了比较,索瑟姆决定用健康人做对照注射实验。1956年5月,他在《俄亥俄州监狱通讯》上刊登广告:医生欲召集25名志愿者进行癌症研究。几天后他竟然征集到96名志愿者,不久增加到150名。
之所以选择俄亥俄监狱,是因为之前这里的犯人曾经非常配合地参与过几次科学研究,有一次还让他们感染可能致命的兔热病。15年后,在犯人身上做实验就要经过审核了,而且被严格控制,因为那时人们意识到犯人无法给予知情同意,他们应被视为弱势群体。可在索瑟姆做实验的年代,全国犯人都被用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比如检测化学武器的效果,再比如判定X射线照射睾丸对精子数的影响。
1956年6月,索瑟姆的同事艾丽斯·穆尔(Alice Moore)用手提袋把海拉细胞从纽约带到俄亥俄。索瑟姆把它们注射到65名犯人体内。杀人犯、盗用公款者、抢劫犯和伪造犯坐在木板凳上排成一排,有人换上了白病号服,有的刚劳动回来,还穿着蓝色工作服。
不久,肿瘤纷纷从接受注射的犯人胳膊上冒出来,和之前在癌症患者身上一模一样。媒体接二连三地报道俄亥俄监狱的英雄,表扬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批同意接受这么严谨的癌症实验的健康人”。他们还引用了一个犯人的话:“如果我说一点也不怕,那是骗人。你躺在床上,想着癌细胞在自己胳膊上长……你作何感想!”
记者一遍又一遍地问:“你为什么报名当志愿者?”
犯人的回答千篇一律:“我对一个女孩做了不可饶恕的事儿,我想我这么做,总能弥补点什么吧。”
“我相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这么做算是为我之前的罪行做了一点补偿吧。”
索瑟姆给每个犯人做了多次注射,和之前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不同,这些人靠自身免疫力战胜了癌细胞,而且注射次数越多,他们的身体做出反应就越快,就好像产生了免疫力。索瑟姆公开了他的结果,媒体疯狂地大肆宣传,称此项研究有可能带来抗癌疫苗的大突破。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索瑟姆继续用海拉细胞和其他活性癌细胞做人体实验,他前后给600多人进行了注射,其中一半是癌症患者。此外,每个来斯隆—凯特林纪念医院和詹姆斯·尤因医院(James EwingHospital)做妇科手术的病人都逃不过他的手掌。即使做解释,他也就是简单地说是在做癌症测试。而且他真就是这么想的:由于癌症患者排斥这些细胞的速度比健康人慢,索瑟姆认为只要记录排斥发生的时间,他就能发现尚未诊断出的癌症。
经荧光染色的海拉细胞,图片提供:Tom Deerinck。
针对这项研究,索瑟姆在后来的听证会上反复申明:“当然,这些细胞是不是癌细胞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不论什么外来细胞,给人体注射后自然会产生排异反应。使用癌细胞只有一个坏处,那就是公众对‘癌’这个词具有很大的恐惧与无知。”
索瑟姆表示,正因为考虑到这种“恐惧与无知”,他才没有告知病人给他们注射的是癌细胞,因为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照他的话说:“把这个可怕的词和临床实验联系起来,会对病人造成伤害,因为病人可能觉得(有可能对,也可能不对)自己要么得了癌症,要么已经无药可救……这种医学上无关紧要的小细节可能给病人情绪造成很大的影响,隐瞒这种细节……是负责任而且符合医学传统的。”
然而,索瑟姆不是这些病人的医生,他隐瞒的也不是病人的病情。欺骗病人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要是病人知道医生给自己注射的是什么,很可能拒绝参与实验。1963年7月5日索瑟姆同布鲁克林犹太人慢性病医院的医学系主任伊曼纽尔·曼德尔(Emanuel Mandel)签订协议,要用其医院病人做实验。要不是这次合作导致事情败露,索瑟姆的实验还指不定会继续多少年。
索瑟姆打算让曼德尔手下的医生给22位病人注射癌细胞。曼德尔把计划告诉手下,并禁止他们向病人透露注射的是什么,三位年轻的犹太医生拒绝遵命,说他们不会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这种实验。这三位医生都知道纳粹在犹太犯人身上做的实验,也都听说过纽伦堡审判。
16年前,也就是1947年8月20日,美国主持的纽伦堡国际战争法庭对七名纳粹医生进行宣判,判处他们绞刑。罪名是:在未经参与人同意的情况下用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比如把兄弟姐妹缝合成连体婴,为研究器官功能进行活体解剖,等等。
法庭立下十条道德准则来约束全世界的人体实验,也就是日后我们所知的《纽伦堡公约》(Nuremberg Code)。公约第一句便是:受试者必须在未受胁迫下自愿同意。这个概念是前所未有的。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中并没有病人知情同意这一项。而且,虽然美国医学学会早在1910年就制定了保护实验动物的条例,但在纽伦堡公约之前竟然没有任何相关法律保护人的利益。
尽管如此,《纽伦堡公约》毕竟只是“公约”,同后来出现的许多公约一样,它们并不是法律,最多只能算是建议。医学院里未必教,包括索瑟姆在内的许多科研人员号称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些听说过《纽伦堡公约》的人,很多以为它是“纳粹公约”,是为野蛮人和独裁者制定的公约,和有良的美国医生没关系。
索瑟姆给病人注射海拉细胞的时间是1954年,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的研究监管机构。其实20世纪初就有政治家尝试把监管条例写入州法和联邦法,但每次都遭到医生和科研人员的抗议。因此,以“阻碍科学进展”为由,这类提案一次次遭到否决。然而在其他国家,早在1891年就有规范人体实验的条款,讽刺的是,在这些国家中,就有德国的前身普鲁士。
唯一能在美国强制推行科研伦理的办法就是通过民事法庭。律师在法庭上可以用《纽伦堡公约》来评判科学家是否符合职业道德。但想把科学家推上法庭并非易事,得有钱、有办法,并且需要知道自己被用于科研实验了。
塔斯基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海拉细胞。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一份民事裁决中。原告是一个名叫马丁·萨尔戈(Martin Salgo)的病人。医生给他施行麻醉,他以为医生要给他做的是一项常规手术,谁知道当自己从麻醉中醒来,竟发现腰部以下已完全瘫痪。医生从没告诉他整个操作过程的风险。法官裁定医生败诉:“医生如果隐瞒必要信息,致使病人无法对即将进行的医疗做出理性判断,那他就没有履行对病人应尽的职责,是有过错的。”他还写道:“医生必须提供足够的信息,这是知情同意的基础。”
“知情同意”强调了医生必须把相关信息告知病人,但是对类似于索瑟姆的研究却没有任何约束,因为索瑟姆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他的病人。得再过几十年,人们才开始质疑,像海瑞塔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有“知情同意”的问题,这次医生是从海瑞塔体内取组织,然后在体外进行实验。
但是对那三位拒不配合索瑟姆的医生来说,未经病人同意便往他们体内注射癌细胞,是绝对违背人权的,也违反了《纽伦堡公约》。曼德尔却不是这么看的。他要一名住院医生代替这三个人给病人注射。1963年8月27日,三名医生集体辞职,辞职信中给出的理由是“违背伦理的科学研究”。他们把信交给曼德尔和至少一名记者。曼德尔收到信,立即把三位医生中的一位叫来,指责他们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背景而过分敏感。
医院董事会成员中有个名叫威廉·海曼(William Hyman)的律师,他并不认为三位医生是过于敏感。得知他们辞职后,他要求查看参与研究的病人的资料。可要求遭到拒绝。另一方面,就在三位医生辞职后几天,《纽约时报》恰好刊登了一篇小报道,标题为《瑞典惩罚癌症专家》,故事主人公是个名叫贝蒂尔·比约克隆德(Bertil Bj?rklund)的癌症研究人员。他利用海拉细胞做疫苗,然后给自己和病人做静脉注射。他的细胞全是从盖伊实验室弄来的,数量庞大,以至于大家都开玩笑说与其拿细胞来注射,还不如把细胞灌到游泳池甚至湖里,然后让人在里面游泳,从而获得免疫。由于用海拉细胞进行注射,比约克隆德被实验室开除。海曼希望索瑟姆也能有同样的下场,因此于1963年12月将一纸诉状递到法院,要求获取该项研究的记录。
海曼把索瑟姆的研究同纳粹研究作比,并从三位辞职医生那里获得供词,他们用“违背法理,违背伦理,可悲可叹”来形容索瑟姆的做法。海曼也从另一位医生那里取得供词,这位医生说:即使索瑟姆问了,病人也不可能给予知情同意,因为其中一位患有帕金森症,不能说话,另外两位只会说意第绪语,还有一个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和抑郁症。无论如何,海曼写道:“他们告诉我没必要签署同意书……那些犹太病人根本不可能同意注射活的癌细胞。”
这件事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医院说诉讼充满“误导和错误”,可报章杂志还是刊出头条新闻:
被注射癌细胞,病人不知情……医学专家谴责注射癌细胞违背伦理
报道说《纽伦堡公约》在美国一贯遭到无视,目前全国还没有保护科研对象的相关法律。《科学》杂志将此事件称为“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关于医学伦理的最激烈的公共争论”,并表示“目前形势对每个人都不容乐观”。该杂志一名记者质问索瑟姆:如果注射诚如你说的那么安全,你为何没有给自己注射?
“我跟你直说,”索瑟姆回答,“现在有经验的癌症研究者屈指可数,即使只有一丁点危险,拿自己做实验也不是明智之举。”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射了癌细胞的病人看到报道,纷纷联系记者。纽约州检察长路易斯·莱夫科维茨(Louis Lefkowitz)也从媒体报道得知此事,随即展开调查。之后,他写了一份五页的报告,其中慷慨陈词,指控索瑟姆和曼德尔有欺骗行为、违背职业道德,并要求纽约州立大学评议委员会撤销二人的医疗执照。莱夫科维茨写道:“任何人都有权决定别人能对自己的身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绝不能剥夺这种权利。病人有权知道……针筒里究竟装了什么。如果知情导致恐惧和焦虑,他们有权表达出恐慌的情绪并拒绝接受注射。”
然而,不少医生站出来,在评议委员会和媒体面前为索瑟姆辩护,说医学界开展此类研究已经有几十年了。他们表示没有必要对科研对象交代所有信息,索瑟姆的做法符合科研领域的职业道德。索瑟姆的律师也辩称:“如果整个领域都是这么做的,那怎么能将索瑟姆的做法称为‘违背职业道德’?”
这件事在评议委员会激起不小的波澜。1965年6月10日,委员会的医疗纠纷委员会裁定索瑟姆和曼德尔“在行医过程中存在欺骗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并建议吊销二人的行医执照一年。委员会写道:“从整个事件过程的记录可明显看出,某些医生认为他们可以对病人为所欲为……病人同意只是可有可无的形式。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委员会在评议中也号召针对临床研究制定更加具体的规范,他们表示:“委员会相信此类规范相当于严肃的警告,以约束科研行为,使其不违反基本的人权和豁免权。”
后来对索瑟姆和曼德尔的处理是,吊销执照暂缓执行,给予一年察看期。然而,这件事似乎对索瑟姆的学术地位没有丝毫影响,察看期一结束,索瑟姆就当选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主席。不过,事件终究在人体实验监管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评议委员会宣判之前,媒体对索瑟姆的负面评价就引起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注意。该机构一直为索瑟姆的研究提供经费,可它早就规定,所有研究人员进行人体实验前必须征得他们同意。索瑟姆事件出现后,国立卫生研究院对其资助的52个研究机构进行了审查,发现只有9个有保护实验对象权利的规定,只有16个会给病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结论是:“对于有病人参与的实验研究,研究人员的判断不足以作为评判该实验是否符合医学伦理的基础。”
此次调查后,国立卫生研究院规定:所有涉及人体的研究必须经过审核委员会评议,判断它们是否符合研究院的伦理准则,其中必须包括受试者签署内容详尽的知情同意书。审核通过才给予经费。而审核委员会应是一个独立的小组,由不同种族、阶级和背景的专家和社会人士共同组成。
科学家纷纷表示医疗研究前途堪忧。其中一位甚至给《科学》杂志主编写信说:“明显无害的人体癌症研究都遭到了制止……1966年将为所有医学进展画上句号。”
同年晚些时候,哈佛大学的麻醉学家亨利·比彻(Henry/">Henry Beecher)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份调查,结果显示,索瑟姆并不孤单,像他一样的反伦理研究足有上百个。比彻把其中最恶劣的22个公之于众,比如,有人曾给儿童注射肝炎病毒,还有人给麻醉中的病人吸二氧化碳,导致病人中毒。索瑟姆的研究名列第17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科学家多虑了。伦理规范的出台并没有阻碍科研的进展。事实上,研究反而突飞猛进,而且其中的很多都要感谢海拉细胞。
选自《永生的海拉》,丽贝卡?思科鲁特著,刘旸译,理想国出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