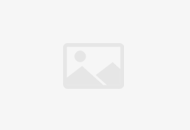历史上的扬州八怪“怪”在哪些地方?其实关于这种问题,历来说法也不一,接下来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从实际看,并不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不平之气,有无限激愤,对贫民阶层深表同情。他们凭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对丑恶的事物和人,加以抨击,或著于诗文,或表诸书画。
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少见,但也不是多见,人们以“怪”来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没有超出当时礼教的范围,并没有晋代文人那样放纵--装痴作怪、哭笑无常。他们和官员名士交流,参加诗文酒会,表现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从他们生活行为中来认定他们的“怪”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只有到他们的作品中,来加以研究。
扬州八怪独辟蹊径的立意
“八怪”(金农、汪士慎、黄慎、李鱓、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径。他们要创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自立门户,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他们的作品有违人们欣赏习惯,人们觉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
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
扬州八怪不落窠臼的技法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
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虞山、娄东等画派,讲求临摹学习古人,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们的创作方法,如“正宗”画家王珲所说,作画要“以元人笔直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们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作品多为仿古代名家之作( 当然在仿古中也有创造),形成一种僵化的局面,束缚了画家的手脚。
扬州八怪挥洒自如的笔锋
“扬州八怪”诸家也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也“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
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
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
扬州八怪特立高标的品行
他们对当时盛行于官场的卑污、奸恶、趋炎附势、奉承等作风深恶痛绝。八人中除郑板桥、李方膺做过小小的知县外,其他人均一生以“鲁连”、“介之推”为楷模,至死不愿做官。就是做过官的郑板桥也与常官不同。他到山东上任时,首先在旧官衙墙壁上挖了百十个孔,通到街上,说是“出前官恶俗气”,表示要为官清廉。
“扬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汇在诗文书画之中,绝不粉饰太平。他们用诗画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郑板桥的《悍类》、《抚孤行》、《逃荒行》就是如此。 “八怪”最喜欢画梅、竹、石、兰。他们以梅的高傲、石的坚冷、竹的清高、兰的幽香表达自己的志趣。其中罗聘还爱画鬼,他笔下的鬼形形色色,并解释说“凡有人处皆有鬼”,鬼的特点是“遇富贵者,则循墙蛇行,遇贫贱者,则拊膺蹑足,揶揄百端”。
这哪是在画鬼,分明是通过鬼态撕下了披在那些趋炎附势、欺压贫民的贪官污吏身上的人皮,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在封建制度极端残酷又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他们却敢于与众不同,标新立异,无怪乎当时一督抚摇头直称“怪哉、怪哉”。邓拓在咏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时曾写道“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可以算作对他们“怪”之特点的总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