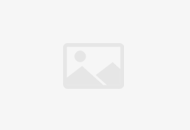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这首《潜龙诗》的作者曹髦,是曹魏第四任皇帝。甘露四年(259年)正月,曹魏宁陵(今属河南商丘)地界的水井中出现两条黄龙,群臣认为这一异象是天降吉祥之兆,纷纷奏贺,而曹髦却认为“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资治通鉴》)。
在曹髦看来,龙乃天子象征,能飞天入海,能吐雾吞云,如今出现于水井之中,与泥鳅黄鳝搅和在一起,左右不能突围,不是困龙、潜龙,又是何意?!借喻抒怀,曹髦作此诗,是对自己身处司马氏控制下,不能一言九鼎,不能朝纲独断,只能屈身做一个受制于人的傀儡,眼睁睁看着皇权旁落而发出的悲凉感慨。表面上,曹髦是在苦闷中自嘲自讽;实际上,此诗一出,他的内心深处已经吹响了战斗号角。
曹髦(241年—260年),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即位前为高贵乡公,是司马师于嘉平六年(254年)废掉曹芳后另立的一个傀儡皇帝。作为曹操的嫡系后人,曹髦血管里流淌着高贵的血液,史籍中称他“少好学,夙成”(《三国志》),能文能武,工诗善画,是“才同陈思,武类太祖”(《魏氏春秋》)的全才。可惜,曹髦生不逢时,英才作傀儡,既是自身的不幸,也是曹魏的不幸。
曹芳被废,皇权扫地,司马得意,改旗易帜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司马氏一旦篡国成功,曹髦这个傀儡或被废,或被杀,终究难逃厄运。事关帝国衰荣,事关个人生死,曹髦岂能甘心受人掣肘,坐以待毙?做一个任人废杀的亡国之君,还是做一个彪炳青史的中兴之主,曹髦在“与诸儒论夏少康、汉高祖优劣,以少康为优”(《资治通鉴》)时,言外之意就表露出了拯救曹魏于水火的愿望。
曹髦登基时年仅十四岁,还是个半大孩子,加之根基尚浅,无力与司马师、司马昭抗衡。即位之处,曹髦面对司马氏兄弟的跋扈,不得不收敛锋芒,迂回对抗,除了做些“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倡导厉行节约的文章外,还有意派人“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噃枉失职者”(《三国志》),看似体恤民情,实则走访调查反对司马氏专权的利己势力。
曹髦的动作和动机,引起了司马氏兄弟的警觉,二人每次领兵远征,必挟持曹髦同往,如司马师在征讨毌丘俭、文钦反叛时,让司马昭坐镇洛阳,自己“奉天子征”(《世语》);司马昭在平定诸葛诞反叛时,索性挟持曹髦和郭太后一同前往,还逼着曹髦下诏“今宜皇太后与朕暂共临戎,速定丑虏”(《三国志》)。司马氏兄弟此举,一防后院起火,二也要让曹髦亲眼看看对抗司马氏势力的下场。
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等势力先后被诛灭,天下已没有曹髦可以依赖的力量,想对付司马氏,也只有靠自己和身边的少许亲信了。曹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英才壮志难酬,无力回天,曹髦越发感到无可奈何。司马师死后,司马昭大权独揽,步步紧逼,不断要求曹髦封赏,提升地位,加速篡国步伐。一首《潜龙诗》,将司马昭比作鳅鳝,暗骂贼臣当道,司马昭见而恶之,有了废掉曹髦之念。
景元元年(260年)四月,已经不满足于“加号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钺”的司马昭又逼迫曹髦为其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离皇帝名号仅一步之遥。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资治通鉴》),不由得怒火中烧,血性激荡。曹髦的生日,为现代阳历11月15日。为了尊严,这位典型的天蝎座皇帝,最终从一个玩偶傀儡升华为一个血性斗士,决定亮剑。宁可战死,决不苟活!
“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这句千古名言即出自此时的曹髦之口。“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当曹髦将诛杀司马昭这一毫无胜算的计划告诉近臣王沈、王经、王业时,他们为求自保,各自散去,“沈、业奔走告昭,呼经欲与俱,经不从”,曹髦瞬间成了讨杀司马昭的孤家寡人。“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惧!……帝遂拔剑升辇,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鼓噪而出”(《资治通鉴》)。
率领区区数百僮仆击讨已有防备的司马昭,无异于以卵击石,飞蛾扑火。即便如此,曹髦毫无畏惧,挺身直前,“帝自用剑”杀敌,结果还是死于敌将成济的戈下,“刃出于背”(《汉晋春秋》),“时暴雨雷霆,晦冥”(《魏氏春秋》),天地为之动容。每次读史到此,笔者都会轻轻掩书,为曹髦之死扼腕叹息,为曹髦之勇热血沸腾。是的,他败了,从他身体喷薄而出的热血却永久地染红了历史。
曹髦死后被废除帝号,“以王礼葬之”(《三国志》),时年二十岁。曹髦即位前为高贵乡公,死后无谥号,史书中仍以高贵乡公称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追谥其为平皇帝。“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洛阳伽蓝记》),他的英勇斗志,他的男儿血性,他的悲壮事迹,无愧“高贵”二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历朝历代众多境遇相同的傀儡皇帝中,曹髦是最有血性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