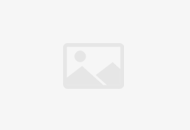夏言,字公谨,号桂洲,明朝中期政治家、文学家,赠少师夏鼎的儿子。为人豪迈强直,纵横辩博,因大礼议而受宠,累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其后被擢为首辅。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刀越磨越硬,越磨越快,并不是什么好事。
嘉靖朝的内阁首辅夏言就是这样一把刀,他是靠两点在大明朝堂上崛起的,一是与宠臣较量,二是揣摩嘉靖的心思。
嘉靖刚即位时,兵科给事中夏言就上疏,希望皇帝上朝以后在文华殿批阅奏疏的同时,能够召见阁臣当面作出决定,“不宜谋及亵近,径发中旨。”
这个建议得到了嘉靖的“嘉纳”。
一击即中后,夏言一发不可收拾,又连续七次上疏,建议嘉靖改革“后宫附郭庄田”,限制后宫及皇亲国戚的利益,奏疏写的掷地有声,朝野传颂一时。
由此引得嘉靖的欣赏与重视后,嘉靖九年,夏言抓住嘉靖的一个心理(由于“大礼议”而怨恨与他对着干的群臣,很想通过改革礼仪制度来彰显自己不容置疑的帝王权威),提出“祀典”建议——改变祖宗旧制,分别祭祀天、地、日、月。
对此,朝臣大多表示反对,此前靠“大礼仪”发迹的宠臣张璁(cong)也在反对者之列,但嘉靖却因此格外眷顾于他。
夏言的这一系列举动,是献媚迎合吗?
是。但与小人的献媚迎合不同。
这一点很重要。
小人献媚迎合往往是越献身段越软,越圆滑。而夏言觉得自己靠的是思辨才华,所以他越是得逞,骨子里越自负,越骄纵。
仗着嘉靖的眷顾,随后夏言便与宠臣张璁展开了较量。
因为张璁“自伐其能,恃宠不让”,嘉靖有意要制约他,加之张璁为朝中士大夫憎恶,几次较量下来,夏言大胜,声望与日俱增,官阶也由给事中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夏言这个人气度不凡,眉目疏朗,胸前美髯飘拂,嗓音洪亮,说话不带乡音。每次经筵开讲,嘉靖都全神贯注,异常欣赏,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夏言明白,要想攀高楼,登顶峰,还必须不断地揣摩嘉靖的心理。在功利心的驱使下,这一阶段的夏言很会拍马屁,嘉庆每次写诗,送给他看的时候,他都要写诗迎合,然后再把嘉靖的诗作制成碑刻送还回去。此外,他时时刻刻窥视帝旨,每次“奏对应制倚待立办”,一副忠心卖力能臣的架势。
这一套手段对嘉靖很管用,不久他即得到嘉靖赏赐的一枚银质印章,上刻“学博才优”四字,使用此印章,可以“密封言事”。
毫无疑问,这是嘉靖要大力提拔他的政治信号。
随着张璁、方献夫相继离开,皇子的诞生,嘉靖对夏言愈发倚重,很快就给了他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的荣誉头衔。
嘉靖十五年,夏言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此时,李时虽为首辅,但决策大权却操于夏言之手,此后入阁的顾鼎臣,又一向以“柔美”著称,不敢对夏言持异议,不过“充位”而已。
经过短暂的微妙过渡,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夏言终于官场登顶,出任内阁首辅。
嘉靖用人有个标准——“不欲臣下党比”,夏言揣摩到这一点,时刻注意标榜自己“不党”的操守。
然而,先恃才敢为,后孤傲自负,极其高调嚣张的夏言忽略了一点,在官场,当一个人有致命缺点的时候,一定会有致命的敌人。
夏言的这个致命敌人就是严嵩。
严嵩虽然比夏言晚六年进入内阁,但却比夏言早十二年得中进士,官场资历实属深厚。但夏言却因为自负嚣张,从不把具有险恶野心的严嵩放在眼里,而严嵩在未寻到攻伐机会前,却是另一副模样,颇懂得忍辱负重,韬光养晦,面对夏言时,他事事保持恭敬的态度,阿谀奉承,唯唯诺诺。
对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如子之奉严君”,好像儿子对待严厉的父亲一样。
而夏言呢,丝毫没有察觉到隐藏在身边的致命危险,不仅如此,因为得势后的极度自负傲慢,夏言对嘉靖也不像先前那样恭顺,尤其对嘉靖沉迷道教玄修,他十分不满,并且有刚直不弯的对抗之举。
嘉靖喜欢穿道袍,戴香叶冠,善于阿谀奉承的严嵩之流会以同样的装扮来讨好皇帝,但夏言却直言“非人臣法服”,有失朝廷体统,拒不跟从,一如既往地身穿朝服。
嘉靖对此十分不满且有厌恶心理,认为这是夏言对他的“欺谤”。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嘉靖借口“天雨伤禾”,亲笔写了手敕,历数夏言“欺谤”、“舞弊”等罪状。严嵩乘机离间,在嘉靖面前,一面顿首,一面泪如雨下地控诉夏言欺辱属下的种种恶行。
嘉靖大怒,不久即将夏言罢官。
夏言罢官后,嘉靖开始把严嵩看作亲信,而严嵩迎合上旨更胜夏言一筹,因写得一手好青词,他越发地受到嘉靖青睐,并很快以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进而又成为内阁首辅。
但嘉靖是个很会操控朝臣的帝王,隐约发觉严嵩过于专横后,他又以一封亲笔信将夏言召了回来,对严嵩加以制衡。
遗憾的是,夏言官复原职后,依然固我,不仅锋芒俱在,而且不拘小节。
举两个例子。
当时阁臣照例有“上官供”,也就是皇帝赏赐的工作餐,严嵩是恭恭敬敬地吃“上官供”,夏言却从来不吃,而去独自享用府中送来的奢侈美食。
内阁加班,嘉庆经常派太监去夜探阁臣动静,夏言全然不顾这些,只要手头事毕,他便从容酣睡,而严嵩却每每挑灯苦干,为嘉靖写青词。
《名山藏》中提及的一个细节更能说明一些问题:嘉靖派太监来见夏言,夏言以首辅自居,从来将太监视同奴仆。严嵩则不然,见到太监,不仅亲切握手,款款请坐,而且还要把黄金塞进太监的衣袖里。
人有时候是被环境杀死的。
见夏言在朝中越来越势孤,严嵩索性勾结锦衣卫头目陆炳,公然陷害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并借此诬称夏言收受曾铣贿赂。
嘉靖闻讯大怒,立刻削夺夏言官职。
起先,嘉靖对夏言并没有萌生杀意,但严嵩却在这时添了两把向夏言索命的暗火。
他暗中派人在京城散布流言,说夏言“心怀怨望”,一向不戴香叶冠是“为朝廷计”,不是为自家计。
完了,他给嘉靖写了封秘密奏疏,用汉朝皇帝杀翟方进的旧事来影射现实,促嘉靖下定处死夏言的决心。
嘉靖二十七年三月,夏言正在回乡途中,见到嘉靖派来的锦衣卫,他惊慌失措地从车上跌下,长叹一声:“吾死矣!”
这一叹,十分地苍凉!
四月,夏言被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他向嘉靖伸冤,但结果换来的却是绑赴西市斩首,妻子苏氏流放广西。
堂堂内阁首辅,未有谋反大罪,亦不是贪官奸臣,最后竟然遭到“弃市”。
可见嘉靖之昏恶,严嵩之阴毒。
当然,这一官场悲剧也有夏言自身的问题,自造险境,不懂如履薄冰。
又或者说,性格决定命运,尤其环境不善不智的时候,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