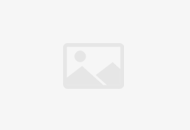柏拉图的乌托邦
柏拉图认为,乌托邦可以有三个阶层,从上到下分别为护国者(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卫国者(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劳动人民(虽然乌托邦内存在奴隶,但是奴隶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乌托邦的领导为哲学王,属于护国者阶层。其建立初还存在立法者阶层,专管立法。阶层是世袭的。在乌托邦社会里,不存在个人幸福,社会无限地强调城邦整体、强调他一己以为的“正义”。在柏拉图眼中,第三阶层的人民是低下的,可以欺骗的。他赋予了统治者无上的权力,甚至统治者“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用撒谎来对付敌人或者公民”。在乌托邦社会里,没有存在坏人的戏剧,没有不是宣传乌托邦的歌曲。在乌托邦里,人成为繁殖工具,男女性的孩子将被集中送到学校进行严格的洗脑式教育。乌托邦内还存在严重的极权主义。
希波达摩斯的乌托邦
公元前494年,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军队破坏并摧毁了在哈里卡纳斯和以弗所之间的城市米勒。因此,以前的居民要求建筑师希波达摩斯(Hippodamus)一次性地把城市重建起来。在那个年代,这是史无前例的情况。直到那时候,城市都只不过是小镇在杂乱中慢慢扩大起来。比如说,阿忒内斯是由混杂的道路组成的,就像谁也没去整体规划过的迷宫一样。要负责整体建造一个中等城市。这就像要在空白纸上创造一个理想城市一样。
希波达摩斯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他设计了第一个有严谨构思的城市。
希波达摩斯不想只勾画道路和房屋。他相信在考虑城市的形状时,同样也可以考虑社会生活。
他设想出一个有1万居民的城市。这些居民分成三个等级:手工业者、农民、士兵。
希波达摩斯希望建一个人造城市,不要有自然的东西。城中心是一个卫城,切割成12部分,就像一个分成12部分的城堡一样。新米勒城的路都是笔直的,广场是圆的,并且所有的房屋都严格地独立了开来,以使邻里之间不会产生什么嫉妒。
另外,所有的居民都一律平等。那儿没有奴隶。
希波达摩斯也不想要有艺术家。他认为艺术家部很难琢磨,是产生混乱的种子。诗人、演员和音乐家都被驱逐出米勒城。那个城市同样也不允许有穷人、单身汉和游手好闲者在内。
希波达摩斯的设想在于使米勒城成为一个永远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完属于美机械体制。要避免所有的危害,就不能有改革,不能有创新,不能有什么心血来潮。希波达摩斯创造了“有条不紊”的新概念,有条不紊的市民在城市的指挥中,有条不紊的城市在政府的指挥中,政府自己则只能有条不紊地在宇宙的指挥中了。
亚当主义乌托邦
1420年,波西米亚发生了胡斯党人叛乱。那些新教的先驱者,要求德国教士改革和开始庄园主制度。一群更激进的人——亚当主义者从运动中分离了出来:他们不但对教会、而且对整个社会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与上帝接近的最好方式是在与亚当——原罪前的第一个人一样的生活条件下生活。他们的名称就来源于此。
他们在离布拉格不远的莫尔河中的一个岛上定居下来。他们赤裸裸地共同生活着,把所有的财产都充公,尽可能重建“罪孽”前人间天堂的生活条件。
所有的社会结构都被排除出外。他们废除了金钱、工作、贵族、布尔乔亚、政府、军队。他们禁止种地,而用野菜、野果果腹。他们吃素,修行对上帝的直接常拜,不要教堂和中间的教士。
他们当然激怒了其他没有这么激进的胡斯信徒。当然,你们可以简化对上帝的崇拜,但不要到这种地步。那些胡斯党庄园主和他们的军队在亚当主义者的岛上把他们包围起来,把这些当时的嬉皮士屠杀了,一个也不放过。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明了“乌托邦”这个词。希腊字母U,否定前缀;topos,地方,因此“Utopie”(乌托邦)表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东西”,(有些人认为这个词的前缀“eu”,是“好”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eutopie”是指“好地方”)。托马斯·莫尔是一个外交家、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朋友,有大不列颠帝国首相的头衔。
在名叫《乌托邦》的书里,他描述了一个他确切命名为“乌托邦”的神奇岛屿,那里发展着一个田园般的社会,不知道有税捐、苦难扣偷盗,他认为乌托邦社会的优点就是“自由、民主、博爱”。
他这样描写他的理想国:乌托邦不仅自由、民主、博爱,而且无比富有,那里的人都是长相俊美,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乌托邦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岛屿。它被无数黄金与白银装饰着,每天数以百万吨的出产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合金。它有设备完好的港口及船只,还有能够载人翱翔天空的物体。
据说,乌托邦生产力十分发达,科技比其他任何地方起码领先1000年以上,所以,科技、生产力太过超前的乌托邦没有货币,每个人都在市场上各取所需。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的,门上没有锁,每个人都必须每100年搬一次家,目的是为了不让人在习惯中僵化。生产者在工作时间里游手好闲是不允许的。没有家庭主妇、没有贵族,没有仆人,没有乞丐。这就使得每一天的劳动都简化成只有15分钟,但仍然可以生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亩产的粮食数以万吨计,一座工厂生产的产品每天数以亿计。
所有的人都有服一个月工役或选择一个月工役农役的义务,以便供应免费市场。假若通奸或是有逃离岛屿的企图的话,乌托邦公民就失去了他的自由身,成为奴隶。那时,他必须整天劳累,服从老同胞的命令。
因不赞同亨利八世国王的离婚,托马斯·莫尔于1532年失宠,1535年被杀头。
美洲印第安人的乌托邦
北美的印第安人,包括苏人、夏延人、阿帕奇人(Apaches)、克劳人、阿瓦若人、科曼奇人(Comanches)等等,有着同样的社会准则。
首先,他们把自己当作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主宰。他们的部落耗尽一个地区的猎物之前便迁徙,以使猎物能够恢复原状。这样,他们的抽取就不会使地球枯竭。
在印第安的社会标准体制中,个人主义与其说是光荣的源泉,还不如说是耻辱的源泉。谋求自己的东西是猥亵的。大家都不拥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权力,在我们的今天,一个买了汽车的印第安人也知道应该把汽车借给第一个向他借的印第安人。
他们的孩子并不会被迫接受教育。实际上,他们实行的是自我教育。
他们发现了植物的嫁接,并能够利用,倒如进行麦子杂交。他们从橡胶液中发现了防水处理原理。他们懂得制造棉衣,纺织技巧在欧洲无与伦比。他们知道阿斯匹林(水杨酸)、奎宁酸……的有益功效。
在北美印第安社会中,没有世袭的权力,也没有永久的权力。对每一个决定,每个人都在部落会议其间提出自已的观点。这是最早的议会制度(比欧洲的共和革命要早得多)。假若大多数人都不信任他们的首领了,那首领就自动退位。
这是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当然会有一个首领,但只有自发地跟随你时你才是首领。对于部落会议接纳的建议,只有投票通过时大家才要遵从。有点像我们社会中一样,只有找到正确的法律才能实行!
甚至在他们的显赫时代,美洲印第安人也从来没有过职业军队,但是战士首先是作为猎人、耕作者、一家之主而被社会认同的。
在印第安的体制中,所育的生命,不管他外表如何,都值得尊重。所以他们爱惜敌人的生命,以使他们也这样做。永远是这种互利的想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战争被当作是人们应该在那儿展示勇气的游戏。人们不希望给对手造成物质上的破坏。战士间战斗的目标之一是用圆形的棍棒末稍去触及敌人。这是一种比杀掉他还要强烈的光荣。他们计算着“触及”的次数,一旦流血,战斗就停止了。很少有人死亡。
印第安人之间战争的主要目标在于偷敌人的马匹。从文化上讲,他们很难理解欧洲人所用的群众战争。当看到白人把所有人都杀掉,包括老人、妇女和小孩时,他们会惊讶万分。对他们来说,这不仅可怕,简直就是变态,不合逻辑,不可思议。但是,北美印第安人抵抗的时间相对较长。
南美社会比较容易攻击。只要把首领斩首,整个社会就崩溃了。这是等级和集权管理制度的大弱点。用他们的君主就能够制服他们。在北美,社会有一个更光彩夺目的结构,那些牛仔们跟几百个移居部落打交道。没有一个不变的大国王,但却有几百个可变的首领。假若白人征服或破坏了一个有150人的部落,那他们必须再一次攻击第二个150人的部落。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种大规模的屠杀。1492年,美洲印第安人有1000万。1890年,他们是15万,大部分都因西方人带来的疾病而死去。
1876年6月25日,小大浩战争时,人们组成最大的印第安人联盟:1万到1.2万个人当中有三四千是士兵。北美印第安人的军队把居斯特将军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在这样一片小土地上很难供养这么多人。因此,胜利以后,印第安人就解散了。他们认为受到这样的侮辱以后,那些白人再也不敢不尊敬他们了。
实际上,那些部落一个个地减少了。直到1900年,美国政府还企图消灭他们。1900年以后,政府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会像黑人、奇卡诺人、伊朗人、意大利人一样融合进多种族国家。但这只是一个短见而己。美国印第安人完全不明白他们能够从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中学到什么,他们认为这些制度明显没有他们的制度先进。
拉伯雷的乌托邦
1532年,弗朗梭瓦·拉伯雷《巨人传》中描写了泰莱姆修道院,提出了他对理想的乌托邦城的个人看法。
不要政府。因为,拉伯雷想:“一个人连他自己都管不了,又怎么能去管其他人呢?”没有政府,那些泰莱姆修道者以他们的意愿行事,以“为所欲为”为箴言。泰莱姆修道院的主人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只有具有良好出身、不受精神约束、受过教育、有德行、好看自然的男女才能被接纳,女人10岁进入,男人12岁进入。
白天,每个人都干他想干的事情。如果他高兴的话就工作,要不然就休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时钟被取消了,避免了时光流逝的概念。人们随便什么时候起床都行,饿了就吃饭。骚乱、暴力、打架都被肃清,安置在修道院之外的佣人和手工艺者担负着繁重的工作。
拉伯雷描绘着他的乌托邦。修道院必须在声瓦尔边上的波·于奥尔森林里建起来,它包括9332个房间,没有围墙,因为“围墙供养阴谋”。6个直径60步的圆形塔楼。每一个建筑物都有10层高,一个直通河流的排污下水道,很多个藏书室。一个林荫交错的公园,中间是一道泉水。
拉伯雷不是受骗者。他知道,他理想的修道院将不可避免地被蛊惑人心的宣传、荒谬的意见和争执或仅仅是被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所摧毁,但他坚信这仍然是值得一试的。 [2]
夏巴泰·泽维的乌托邦
那些波兰犹太教神秘哲学家在对《圣经》和犹太教法典进行了反复地研究和深奥地阐释之后,预言弥赛亚①会在1666年出现。当时东欧的犹太民族正处在低谷时期。几年前哥萨克公选首领博格当·克默尔尼斯基领导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波兰封建大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由于无法攻破统治者坚固的堡垒,杀性答起的暴民们就把被认为忠于封建君主的犹太村镇作为报复对像。几周之后,波兰贵族也发动了血腥的报复性袭击。犹太村镇又一次遭到洗劫,死伤者不计其数。
“这预示着哈米吉多顿决战②的来临。”犹太神秘哲学家如是说。“这是弥赛亚降临的前兆。”
【① 弥赛亚:救世主。】
【② 哈米吉多顿,基督教《圣经》中所说的世界末的善恶大决战。】
正是在这时夏巴泰·泽维出现了,这位目光炯炯有神、温文尔雅的青年自称就是弥赛亚。他能说会道,安抚答众,让他们心中依然拥有希望。人们断言他能够创造奇迹。在东欧各犹太团体中立刻兴起一股强烈的宗教热忱。然而许多犹太教教士指责他为“篡权者”和“伪国王”。在夏巴泰·泽维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宗教分歧,许多完整的家庭由此分崩离析。但是,仍然还有数百人决定抛弃一切,离开家人去追随这位新的弥赛亚到圣地建立一个新的乌托邦社会。
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多久。一无晚上,土耳其素丹派出的奸细绑架了夏巴泰·泽维。他最后免于一死,但却归依了伊斯兰教。他信徒中最最忠实的几个一直跟随着他,而其他人更愿意把他给忘记。 [3]
傅立叶的乌托邦
夏尔·傅立叶是个呢绒商的儿子,1772年出生于贝臧松。从1789革命起,他就表现出对人道的惊人志向,他想要改变社会。1793他向督政府成员解释他的设想,但遭到他们的讥讽。
从此他便决定过平淡的家庭生活,成为出纳员。当有空闲时,夏尔·傅立叶仍追求着他固执的念头,寻找一个理想的世界。他在几本书中描写了最微小的细节,包括在《社会化工业化新世界》里。
这个空想者认为:人应该在1600到1800个成员的小共同体中生活。用这个被他称作法朗吉的共同体来代替家庭。没有家庭,便有更多的亲属关系,更多的权力关系。政府被缩小到最低的限度。每天大家都一起在中心广场上作重大决定。每个法朗吉都住在一个被傅立叶叫作“法伦斯泰尔”的城居中。他非常确切地描写了他理想的城居:一个三至五层的城堡。底下的道路夏天通过洒水而凉爽,冬天通过大壁炉而暖和,在中央有一个治安塔,那里有了望台,排钟,查普电报,夜岗。
他想把狮子和狗进行杂交,创造出一种新的驯良品种。这些狗狮同时用来当坐骑和“法伦斯泰尔”的看守者。
夏尔·傅立叶用信把他的想法寄往世界各地。他坚信,假若人们都照它实行的话,法伦斯泰尔的居民就会自然进化,而且可以在他们的器官上看出来。这种进化尤其是表现为:胸脑上长出第三只胳膊。
一个美国人按傅立叶的设想建立了一个忠实的法伦斯泰尔。由于建筑上的问题而彻底失败了。用大理石墙造的猪圈是照管得最好的地方。但问题是人们却忘掉了要准备门,最后只好用起重机把猪吊进去。
傅立叶的信奉音所造的类似的法伦斯泰尔或是同一思想的共同体到处都有,尤其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美国。
傅立叶死时否认了他所有的信徒。
曙光城(黎明新村)
曙光城位于印度蓬笛谢里(译者注:印度中央直辖区,1962年由蓬笛谢里,加里加尔、亚南、和马埃4个前法国殖民地组成)附近,它是历史上几次最有意义的乌托邦公社实践地之一。
1968年,孟加拉哲学家斯里·奥罗宾多·高斯和法国女哲学家米拉·阿尔法萨(主母)着手在曙光城创建一座理想村。按他们的设计,其外形应酷似一个星系,光从中央的球状部分射出,照亮村内各处。两位哲学家等待着各国人士前来。后来,在这里生活的主要是一些寻求绝对乌托邦的欧洲人。
公社里的男男女女们造起风车,盖起手工工场,开挖水渠,还建了一座砖厂和一个信息中心,并且在这个气候干燥的地方种植了农作物。“主母”在此期间著了好几本书,详细叙述了她的思想及体验。
一切都在向乌托邦的理想不断靠近,直到有一天,有些社员要求在“主母”的有生之年尊奉她为女神。“主母”婉言拒绝了这项殊荣。可那时,斯里·奥罗宾多已经去世,再也没有人在她身边支持她了。“主母”无力违抗这些崇拜者们的意志。
他们把她禁闭在房中,认定“主母”既然不愿做活的女神,那就让她做死的女神。也许她不曾意识到自己体内神的特质,但在别人眼里,她自始至终都是个女神。
“主母”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显得十分沮丧消沉,像是经受了重大的打击。每当她想提及自己被禁闭在房中受尽崇拜者们的种种虐待时,这些人就会立刻打断她的话语,并将她带回房中。在这些自称无比尊崇她的人日复一日的折磨下,“主母”渐渐变成了一个又干又瘪的老太婆。
其实,“主母”也曾向从前的朋友们秘密地传出消息:有人想毒死她,把她变成一尊死的女神,让她更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可是,她的求救始终都只是徒劳,所有想帮助她的人都被立即赶出了公社。她最后只得呆在房中,空对四壁奏响风琴,聊以倾吐心中的凄苦,诉说自己的悲剧。
再怎么努力也是无济于事,1973年“主母”可能是由于服用了大量的砒霜,离开了人世。曙光城以女神之礼为她举行了葬礼。
失去了“主母”后,再也没有人能把公社凝聚成一体了。公社分裂了!所有的社员互相倾轧,将乌托邦这一理想之国的概念完全抛诸脑后。他们在法庭上长期争执不下,一件又一件的诉讼令人不禁生疑:这还是那个人类历史上最富有雄心壮志,最为成功的乌托邦之一吗?